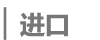〔譯者按〕韋伯的《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篇曾長期被忽視,但晚近卻越來越受到學界重視的文章。與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樣,這也是他在1904年訪美后的成果,而且主題也相互關聯。此文主要從宗教組織的角度來談論資本主義倫理的可能性,有人誤以為韋伯此文與《新教倫理》中的看法相矛盾,這是不對的。實際上二者互為補充,忽視這一點,也很容易導致對《新教倫理》一書產生誤解。韋伯在去世前不久編訂的最后著作《宗教社會學文集》中,就將《新教倫理》和《新教教派》并列放在第一部分,可見在韋伯心目中,這兩文是具有同等重要位置的。過去對于韋伯的學說,曾有精神因素和制度因素兩種不同的理解路向,但此文至少可以告訴我們,實際上在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上,韋伯從一開始就是雙向思考的。這有助于我們完整理解韋伯的學說。此文迄今只有唯一的一個英譯本,收入斯蒂芬·凱爾伯格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新譯本之中,筆者因此將凱爾伯格所作全書〈導論〉中關于此文背景介紹的一節也譯出(但刪去了一些無關的注),以便于讀者更好理解韋伯此文。關于韋伯此文的翻譯,有兩點需要說明:
(1)原文注解體例不統一,除尾注外還有部分腳注,筆者將其統一為尾注形式,部分次序也作了相應調整;(2)韋伯文中所提到的一些術語及專名,一般人殊難理解,筆者視乎必要在文中以[注-]的形式加以解釋。另外,香港浸會大學宗教系費樂仁(Lauren Pfister)教授在此文翻譯過程中提供了寶貴幫助,謹此致謝。
英譯本導言:韋伯的“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注1)
斯蒂芬·凱爾伯格(Stephen Kalberg)
本書中重印的“教派”一文(頁127-48)是寫于韋伯從美國返回德國后不久。以簡寫形式在1906年的兩份報紙發表(注2),他現在試圖讓更多德國聽眾接觸到他。通過1904年與美國近距離接觸[得到]的看法,韋伯希望對德國流行的種種陳詞濫調作一番影響。
“教派”一文更沒有《新教倫理》那么學術化。此文通過在美國中西部、南部、中大西洋各州及新英格蘭地區的旅行,反映了韋伯敏銳的社會觀察,不過其筆調沒有那么正式。盡管如此,他輕快的評論并不應被視為僅僅是要提供碎片式的“美國生活印象”。相反,韋伯通過對美國清教信仰在其起源250年后的命運,向他的讀者進行了追溯。
一方面,《新教倫理》提供了一個對具有特定宗教教義的信仰者的歷史調查,也通過對救贖的研究俯瞰了虔誠的內在心理動力與焦慮,還詳細描繪了支配美國、英格蘭、荷蘭和德國十七、十八世紀經濟行動之信仰和牧師實踐的影響。另一方面,“教派”一文則在二十世紀的開端考察了美國禁欲新教主義對社會群體的影響。韋伯涉及了團體成員資格之獲得與喪失的社會心理學,甚至還有它們與禁欲新教對工作與經濟行動的影響之相互關系。資本主義精神現在甚至比福蘭克林時代更加“入世”,韋伯希望簡短地歸納其主要影響。通過這種方式,“教派”一文補充了《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的探討,以及在有關信仰和行動之關系方面,天主教、路德教和清教之間的差異。因此,本書也將此文收入。
韋伯在“教派”一文中保持了一個穩定的視角,把問題集中于“[美國社會中]一度在所有禁欲主義教派中廣為流行的那些條件的直接派生物、剩余物和幸存物。”韋伯認為,“教派精神”具有多重遺產,它們構成了許多現象的社會學基礎,如社會信托、對世俗權威的懷疑態度、自治的實踐、還有美國人構筑公民團體的敏捷能力。
在此文中只談論了教派精神晚近的剩余物。韋伯強調,對于一個人加入某個社會團體的資格要檢驗其尊嚴、誠實和好的品質的觀念,新教教派是這一觀念最初的社會承擔者。作為“排他性”的組織,最初的教派只有在純粹的信仰基礎上才允許成員的加入。在作出決定之前,對于成員的道德品質要做嚴格考察。所以,一個人要是有正派的名聲的話,那自然就會擁有成員資格。教派能夠對其成員施加直接的社會影響,使他們不至于受誘惑偏離正道,正因為此,教派具有了證明其成員高尚行為的資格。
美國在1904年佩戴其標識所屬的世俗俱樂部或社團的徽章與領針,韋伯認為,這些東西和教派成員資格的作用相似,在建立在社會榮譽和個人德性方面吸引著人們。加入某個民間社團甚至就意味著人的社會地位的提升;這些人現在具有了可信賴的資格和“紳士”的角色。事實上,如果人們希望能在一個社區里被充分接納的話,這種成員資格是必不可少的。禁欲新教主義的影響在1904年作為“涉入”和“服務”社區的規范而明顯存在,由此,它在遙遠的國家和孤獨的個體“之間”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間團體。教派精神的這一成就構成了美國社會的一種基礎,使美國社會獨一無二地偏好創建許多這樣的團體。(注3)反過來,在其政治參與文化上和自治方面,這種能力構成其核心要素。
今天,大量的“規則”和各式俱樂部開始部分地承擔了宗教共同體的功能。幾乎所有對自己考慮的小商人都在其領子上佩戴某種徽章。不過,作為對個人“榮譽”的保證,這種形式的所有原型實際上都是教會共同體。(注4)
對于韋伯來說,“沒有人會懷疑清教主義在美國生活方式上的決定性作用。”
為了勾畫出美國社會圖景的這些特質,韋伯希望向德國普遍持有的那些陳腐之見挑戰,并在更廣的意義上,向德國人對于“現代社會”的共同觀感挑戰。在歐洲這樣一種信念廣為流行:資本主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將個人從“共同體”(Gemeinschaft)中割裂開來,使他們飄浮不定,并將其與“社會”(Gesellschaft)的其他人[的聯系]切斷。沒有了活生生的社會聯系,人們無目的地飄蕩,就像“原子”一樣互不聯系。對于涂爾干(Emile Durkheim)來說,這種情況導致了社會的反常和自殺率的提高。另外有些人談到了現代生活的“匿名”(anonymity)
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這樣看美國,他們認為這個國家實現了資本主義的最快速發展,正因為如此,美國社會一定是由一群缺乏個性、與他人缺乏非市場式聯系的個人組成的“沙堆”(Sandhaufen)。韋伯注意到美國中有組成社團的廣泛傾向,尤其重要的是這些東西源于(由其獨一無二的宗教傳統而來的)成員資格,因此韋伯希望向歐洲人的這種陳腐觀念徑直挑戰。此外,作為一個注重具體事實而非普遍“發展規律”的社會科學家,韋伯希望可以在資本主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共同經驗之外,另外找出,現代國家是如何作為系于宗教的特定歷史遺產之結果而變遷的。通過對不同具體事實的分析,韋伯認為,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有其自身的道路。對于他的德國同胞而言,韋伯希望告訴他們,盡管德國人對于自己國家的“原子化”社會抱有夢魘般的情結,但是這種現象的根源不是別的,它部分地就是源于德國的特定歷史與文化力量的聚合。
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上)(注5)
作者:馬克斯·韋伯
在美國,“政教分離”的原則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了。這種原則被執行得很嚴格,以至于沒有一個公認的官方宗教,對于國家來說,甚至要求公民接受某一種派別[的宗教]也被認為是違法的。對于宗教組織和國家政權間的關系之原則(注6),我們這里并不想討論其重要性。我們所感興趣的只是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僅僅在25年前,“無教派歸屬感者”的數量估計不過6%左右而已(注7);事實還在于,美國沒有像大多數歐洲國家那樣,為了賦予某一特權教會以歸屬感而給予它們高額的有效[國家]補貼,而且美國同時接受了大批的移民進入。
此外還應當看到,在美國教會的歸屬感與德國比起來,帶有更多地經濟上的負擔,尤其是對窮人而言。已公開的家庭預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埃瑞(Erie)湖的一座基本上完全由德國伐木工移民構成的城里,我個人聽到了許多關于在圣會中這種負擔的例子。以平均年收入1000美元計的話,他們出于宗教目的的定期奉獻幾乎為每年80美元。每個人都知道,在德國,甚至只要有這樣一筆數字的一小部分,都將會導致教會信眾大批流失。但是非常不同的是,在美國十五年到二十年前都從沒發生過這樣的事,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家最近越來越歐洲化以前,在所有沒有充斥歐洲移民的地方,這種緊密的教會意識都是隨處可見的。(注8)每一個以前的旅行者都指出,在美國正式的教會意識[的存在]是無可質疑的,和最近幾十年比起來,以前還要遠為強烈得多。我們在此對于這種情況的某一方面表示了特殊的興趣。
僅僅一代人前,當商人們自我組織起來并訂立新的社會契約時,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你屬于哪一個教會?”這個問題被一種并不魯莽且看來適當的方式問出,但是它肯定不會被隨意地問。在紐約的雙子城布魯克林,這一老傳統仍以相當大的程度被保持著,而且在那些越少受到移民影響的地方,這一情況就越突出。這一問題使人們想起了典型的蘇格蘭客餐(table d’h·te),四分之一世紀前,那兒的歐洲大陸人幾乎總是要面對這樣一種情況:一位女士問你,“你今天參加了什么侍奉?”或者,要是那些歐陸人作為最年長的客人而出現,且碰巧坐在最前方的凳子上的話,侍者在端著湯過來時將會請求他,“先生,請[領我們]祈禱。”在Portree(Skye)這個地方,在一個美麗的星期天我就碰到了這樣的問題,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說法,只有這樣說,“我是一個Badishe(注-德國南部地名)國教會(Landeskirche)的成員,在這里沒有看到我的教會的聚會。”那位小姐對這個回答很高興也很滿意,“哦,除了他本人的派別,他不參加任何侍奉。”
如果人們對于美國的這一情況觀察得更真切得話,他會很容易看到,在社會生活和商業生活中總是要牽扯到宗教歸屬的問題,這兩種生活是需要持久而信任的關系作為基礎的。但是我們前面也指出,美國政府并不介入這個問題。這是為什么?
首先,[自1904年來]一些個人觀察也許可以對此加以解釋。在一段臨近印第安區域的鐵路形成中,該作者坐在一位旅行的“殯葬所硬件”(即墓碑上的鐵字母)商人旁邊,偶然提及了依然非常強烈的教會意識。于是該商人這樣說,“先生,在我們這里,只要他喜歡,每一個人都可以信或不信;可是如果我要看到一個農夫或商人根本不屬于任何教會的話,我會連五十美分都不借給他的。如果他什么都不相信,那憑什么相信他會還錢給我?”這里的動機有一點兒模糊。
從一個德國出生的鼻喉專家的故事那里,問題會更為清楚一些,他在俄亥俄河邊的一座城市里開業,他向我說了他的第一位病人就診的事情。應醫生的要求,他躺在沙發上,接受鼻探測器的檢查。病人一站起來就莊嚴地作出強調,“先生,我是某某大街某某浸信會的成員。”醫生很困惑,這對鼻子的病和他的診斷有什么關系嗎,所以他謹慎地從一個美國同僚那里打聽。這位同僚微笑著告訴他,病人對自己教會的陳述僅僅意在告訴他:“不必擔心費用。”但是為什么要說得這么精確呢?或許這從第三個事件中可獲得更明白的理解。
在十月份一個美麗晴朗的星期天下午早些時候,我參加了一個浸信會的浸禮儀式。我同幾個親戚在一起,他們是來自幾英里外北卡羅林納州M縣偏僻地帶的工人。浸禮在一個池塘里舉行,池塘是由出自藍脊山脈(Blue Ridge Mountains)的一條小河注成的,老遠就可以看見。天氣很冷,夜晚還會結冰。大群的農民家庭都圍站在山坡之上;他們坐在自己的輕型兩輪小馬車中,有的來自鄰近,有的則來自大老遠。
穿著黑袍的布道者齊腰深地站在塘里。經過了不同的準備后,大約男女各十人穿著他們最好的衣服,一個接一個的進入了池塘中,他們見證了他們的信仰后就被完全浸入水中,婦女扶著牧者的手。他們起來之后,穿著濕衣服直哆嗦,然后步出池塘,每一個人都向他們發出“祝賀”。他們很快被裹上了厚厚的毯子,然后返回家中。我的一個親戚[對此]這樣評論,“信仰提供的無窮保護可以防止打噴嚏。另一個親戚站在我身邊的親戚,按照德國傳統來看是無教會的,他看著,鄙夷地向上唾了一口。他沖一個受浸者說,“喂,比爾,那水不冷嗎?”回答是異常熱情的,“杰夫,我心里有一些火熱的地方(地獄嗎!),所以我一點也不覺得冷。”在為一位年輕人受浸時,我的親戚大為吃驚。
“看吶,那家伙,”他嚷道,“我向你提過。”
浸禮結束后我問他時,他說,“為什么你希望那個人會受浸?他想在M縣開銀行。”
“在他周圍難道不是有許多浸信會徒可能做他的客戶嗎?”
“不全是這樣的,一旦受浸,他就會獲得整個地區的資助,他將會在競爭中壓倒每一個人的。”
在接下來關于“為什么”和“以什么手段”的問題中,產生了下面的結論:本地浸信會的接納只會導致接下來最謹慎的“審查”,然后會細致調查直到你的孩提時代的行為(瘋狂行為?經常上酒店?跳舞?看戲?打牌?過早出現債務?其他的荒淫行為?)。圣會仍然是嚴格堅持宗教傳統的。
圣會的接納被認為是一位紳士道德素質的絕對保證,尤其是那些商業活動中所要求的素質。浸信會把整個地區的存款都系于個人,并在沒有任何競爭的情況下給予他無限的信任。他是一個“被造的人”。進一步的觀察也證實了這些,至少情況是很相近的,在許多不同的地方都是如此。一般來說,只有那些屬于循道宗、浸信會或其它宗派,或者類似的非國教徒秘會的成員才會在商業上獲得成功。當一個宗派成員搬到另一個地方,或者他是一個流動商販時,他身上負有他所屬圣會的委任狀;這樣他會發現不僅與宗派[其他]成員能容易地接觸,而且首先,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尋得信任。如果他本人在經濟困難的時候沒有舞弊行為,那該宗派就會替他安排事務,向債權人[替他]作擔保,并在任何地方都幫助他,其根據一般都來自圣經的律令,mutuum date nihil inde sperantes [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路加福音6:35)
債權人的想法是這樣的,對方所屬的宗派為了自己的威望,不會讓債權人在代表該宗派的成員那里遭受損失;不過這一切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具有決定性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具有良好聲譽的宗派只可能會接受這樣的成員:他們的“行為”毫無疑問使他們獲得了道德聲譽的保證。
至關重要的是,宗派成員的身份就意味著一份道德素質的保證書,尤其是對個人的商業道德而言。與那些一個人“天生”就是其成員并被賦予超越義和不義之類榮耀的“教會”相比,這一點是截然不同的。事實上,一個教會就是一個組織榮耀、管理宗教恩典的公司,就好比一個捐款基金會那樣。僅僅從原則上而言,教會的歸屬感是義務性的,對于成員的素質它并不能證明什么。不過,一個宗派是一個自愿者組成的團體,它的成員原則上只包括那些宗教和道德上合乎規范的人。如果一個人發現他的成員資格在經過宗教上的審查之后,得到自動接受,那他就是自愿地加入了該宗派。在美國,這種選擇[的效果]經常被那些競爭性宗派導致的靈魂改宗而強烈地抵消――這部分的是強烈地受布道者的物質利益所影響,這當然也確是一個業已存在的事實。所以,在各個競爭性的教派之間,也經常存在著限制改宗的聯合協議。這種協議的形成可以看一些例子,如某個人已經離了婚,可是其婚姻從宗教觀點來看是無效的,為了防止這種人[鉆空子]輕易結婚,就會制定那樣的協議。那些較容易再婚的宗教組織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一些浸信會團體據說有時候在這方面比較松,而天主教和路德宗則以其嚴格規定而受到稱贊。不過據說這種立場也導致了這兩個教會的成員減少。
如果因為道德上的過錯而導致被所在宗派開除,這將意味著在經濟上喪失信譽,社會上喪失其地位。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1904)中,無數的觀察都表明,不僅教會意識本身正在快速消亡(盡管它仍然很重要);而且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非常重要的資質也可以確定是如此。在大都會地區,我在幾個隨便了解到的事件中都得知,那些對一塊未開發的地產打主意的投機商的常見做法如此:做出一副最謙卑的樣子,常規性的建立一座教堂;然后他從某一所神學院中雇用一個代理人,付給他五、六百美元,如果這個人能召集聚會,并使這個教堂滿堂的話,就把他安到像牧師這樣的顯赫位子上。我見到過明顯失敗并破落的教會。不過大部分情況下,牧師們據說都是成功的。諸如主日學校(Sunday School)之類的睦鄰聯系方式對于一個初來者而言,還是必不可少的,不過首先還是要與“道德上”可靠的鄰居相聯合。
在其它方面,不同教派之間的競爭也很激烈,如在聚會的晚點上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奉獻。在上流社會的教會中,音樂上的表現也和這種競爭有關。(如波士頓三一教會的一個男高音,他據說只在星期天唱,且收入8000元。)盡管有這樣激烈的競爭,各個教派之間的相互關系還是友好的。例如,在我所出席的一個循道宗的侍奉中,我前面提到的浸信會的浸禮儀式被當作一種壯觀而介紹給每一個人,以圖啟發他們。主要的是,這些圣會完全拒絕聽“教條”布道和自白式的特性。它們所唯一提供的是“倫理”。在那些我所聽到的面向中產階級的布道中,講道具有典型的布爾喬亞道德風格,毫無疑問是令人敬仰而又穩重的,同時又是以最溫和、最清醒的方式進行的。但是這些講道所傳達的是明顯的內在信念,布道者也經常被打動。
今天,[所屬]派別的種類是相當無關緊要的。一個人是共濟會成員,基督教科學主義者,基督再生論者還是貴格派成員,或者都不是,這些都是無所謂的。(注9) 決定性的因素在于,一個人在德性上經過一番檢查和倫理審查之后,經過“投票”被接納為一名成員,所依憑的是新教入世禁欲主義、因而也是古代清教傳統的道德要求。[現在]還可以看到相同的影響。
更詳細的調查還揭示出,存在著以“世俗化”為特征的穩固過程,源于宗教的所有現象都屈從于現代社會。不僅僅是宗教社團(當然也有宗派)對美國社會生活有這樣的影響。不過,教派的這一影響是逐步而緩慢衰退的。如果人們稍加注意,就會注意到醒目的事實(甚至十五年前就已出現了),在美國的中產階級(他們總是生活在十分現代化的大都會地區和移民中心之外)中間,有非常多的人在紐扣眼上裝了一個小徽章(五顏六色的),它讓人很容易就會想起法國榮譽軍團的玫瑰型飾物。當問這是什么時,人們一般會把它和某個帶有冒險和狂熱意味的名字相聯系起來。很明顯,它的重要性及其目的是這樣的:幾乎所有的團體在除了提供許多不同的侍奉外,還有安葬保險的功能。但是經常的,尤其是在那些最少受到現代裂變影響的地方,這些團體給成員提供了給予兄弟情誼般幫助的倫理教誨,這種幫助是每個成員都能做到的。如果他遭遇了并非自己造成的經濟困境,他可以做出這種吁求。這次我就注意到了一些這樣的例子,這一教誨所遵循的原理就是:“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或者至少其中很少利益因素。很明顯,這樣的教誨是具有兄弟之誼的成員們所愿意認可的。此外,一個主要的問題是,成員資格的重新獲得要通過對道德價值的調查和肯定,并經由投票表決。所以在紐扣洞上的徽章就意味著,“我是一個經過了調查和審查而得到紳士身份的人,我的[教派]成員資格保證了這一點。”而在商業生活中還首先意味著:通過了信譽保證的檢驗。人們可以看到,商機經常受到這些正當性的決定性影響。
所有這些現象都基本上限定在中產階級層面,不過它們似乎正在處于快速裂解之中,至少對于宗教組織是如此。一些有教養的美國人常常簡單地忽略了這些事實,或帶著一些憤怒鄙之為“騙局”或倒退,或者壓根就否定這些事實;許多人實際上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威廉詹姆士向我確證了這些事情。不過這些[傳統]的幸存者在許多不同的地方仍然存在,有時候其形式顯得有些怪異。
這些團體是典型的通往上層社會的交通工具,它們由企業界的中產階級人士圈子人士組成。它們所起的作用是,在中產階級的廣泛階層(也包括農場主)中,散布并維持布爾喬亞式的資本主義商業倫理。
眾所周知,在美國的億萬富翁和信貸大亨的“帶頭人”(promoters)、“工業領袖”中有不少人(最好說是老一代人中的大多數),他們在形式上是屬于這些教派的,尤其是浸信會。不過,本質上而言,這些人經常是由于純粹的傳統因素而聚到一起的,和在德國一樣,這樣做是為了使自己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獲得正當性,而不是使自己作為商人而取得正當性;在清教時代,諸如此類的“經濟超人”并不需要這樣的支撐,他們的“宗教虔誠”當然也時常是非常模棱兩可的。首先是正在形成的中產階級、或從其中往上走的階層,成為了那些特定的宗教導向的承擔者,人們實際上可以把他們中的一些人看作是僅僅由偶然因素決定的。(注10)
不過我們一定不能忽視,如果沒有一種生活方式的原則和這些資質的普遍存在,如果不是這些資質通過宗教團體而得以維持的話,即便在美國,今天的資本主義也是不可能像它本來的樣子的。在任何經濟領域的歷史中,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夠塑造出像摩根(Pierpont Morgen)、洛克菲勒、古爾德(Jay Gould)等那樣的資本主義形象來,[這不同于]封建主義和家父長主義時代的僵化。他們所用以掌握財富的唯一的技術手段已經改變了(當然如此!)。他們屹立著,站在“善與惡的彼岸”。但是,不管人們對他們在經濟轉變中的重要性估計得有多高,也不能無限夸大,在主導一個特定時代和特定地區的經濟氣質中,他們永遠也不是決定性的。首先,他們不是特定的西方中產階級氣質的創造者,也不會變成它的承擔者。這里不從細節上討論這些美國宗教派別和許多團體及俱樂部(它們是幾乎獨一無二的)之政治與社會重要性,他們的成員的入會都是經由票選的。在一系列諸如此類的獨一無二團體中,最后一代典型的美國佬的完整生活引導著它們,從學校的男孩會(Boys’ Club 注-指表現男子勇氣的社團)開始,到運動員會或希臘字社團(Greek Letter Society注-指用希臘文來標志自己名稱的社團),或某些方面的另一類型學生俱樂部,接著是許多著名的商業與中產階級俱樂部,最后是大都會的財閥俱樂部。獲得[它們的]承認就等于獲得了向上爬的門票,尤其與在一個人的自我情緒廣場前樹立的許可證差不多。獲得它們的承認也意味著對自我的一種“證明”。一個在校的大學生如果沒有被任何會社(或準社團)所接納,不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如同某種賤民(我注意到有因為未獲接納而自殺的情況)。一個如是的商人、職員、技術員或醫生通常就獲得了毫無疑問的服務能力。今天,無數這類的俱樂部成為了通向貴族地位團體趨向的承擔者,這類團體是當代美國社會發展的特征。這些很有名的地位團體在側面發展,它們與赤裸裸的財閥統治形成了鮮明對照。
在美國,純粹的“金錢”本身也能買到權力,但是卻買不到社會榮譽。當然,它也是掌獲社會尊嚴的一種手段。在德國和任何其它地方都是如此。除了德國之外,[其它地方]社會榮譽的適當途徑來自于對封建地產的購買與繼承,及有名無實的貴族身份的獲得,這些也反過來加速了貴族“社會”第三代的認受性。在美國,老傳統尊敬白手起家的人而不是繼承者,通往社會榮譽的階梯由在某所院校的友誼認同度所構成,從前則是一個特定的教派(例如,在紐約的長老會教會中,人們可以發現軟沙發和扇子)。現在,屬于某一個特定的俱樂部比什么都要重要。此外,這樣的家庭很重要(它們位于那些在中等規模城市里幾乎從來不缺少的“街道”上),那些諸如此類的服裝和運動也是如此。只是在最近,來自朝圣教父,Pocahontas(注-印第安女性名字)與其它印第安婦女等等之類的關系也變得重要了。這里并不欲在細節上討論他們。出現了許多關注重建財閥的家系諸如此類的代理及翻譯機構。所有這些現象――經常非常稀奇古怪,屬于一個歐洲化了的美國“社會”的廣闊領域。
從過去直到現在,具體的美國式民主的一個確切特征就在于,它的結構不同于由許多個人所構成的無定形的沙堆,而是由非常排他但卻又是自愿組成的團體所構成的復雜結構。直到不算太久前,在職務和教育方面,這些團體仍然不認可生來及繼承來的財富之尊嚴,也不承認官方職務與教育文憑的尊嚴;至少在世界上其它地方,他們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還是非常少見的。不過即便如此,這些團體也遠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張開雙臂。可以確信的是,十五年前,一個美國農場主如果不在正式介紹后讓他的客人與工人“握手”的話,他就不會領著客人從他正在犁田的雇農(天然的美國人!)旁經過。
以前,在一個典型的美國俱樂部里,沒有人會記得有這樣的事,如兩個成員會以老板和職員關系一起玩臺球。這里絕對隨處可見的是紳士的平等性。這樣的事在日耳曼-美國俱樂部里也不是經常有。我問過一個在紐約的德國商人(他有著最好的漢薩式的姓名),為什么所有人都試圖獲得一個美國俱樂部的接納,而不是一個設備非常良好的德國俱樂部時,他的回答是,他們(日耳曼-美國人)的老板偶然會和他們一起打臺球,可是僅僅讓他們覺得老板們自我感覺這樣作很“仁慈”。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工人的妻子和工會成員一起吃午飯,她們在著裝和行為上可以隨心所欲,在中產階級女士們看來是有幾許老土和糟糕的式樣。
他希望自己在這一民主內能夠被充分接納,不論自己處在何種地位,他不僅要必須遵循資產階級社會的傳統慣例(包括了對男人著裝的嚴格要求),而且作為一種規矩,他必須能夠顯示出自己成功贏得了某個組織的票選接納,而不論該組織是教派、俱樂部還是友誼會團,這樣他才能為自己獲得充分的[身份]正當性。要在這樣的社團里呆下去,他也必須得證明自己是一個紳士。而在德國的類似組織中,組成的關鍵在于庫魯爾(Couluer)(注11)的重要性、及商業和貿易領域的預備官員委員會、還有通過決斗而獲滿足從而得到高位資格的重要性。它們的性質都是相同的,不過其導向及物質后果就顯著的不同。
如果他沒有被成功接納的話,那就不能算是一位紳士;如果他像在一般的德國人中間那樣(注12),對此表示輕視,那他將會不得不走上一條坎坷之途,尤其是在商業上更是如此。
但是盡管如此,我們這里并不想分析這些條件的社會意義,這一點前面也說過了,它們牽涉到深刻的轉型問題。首先,我們感興趣的事實是,需要經由票選入會的世俗俱樂部和社團的現代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世俗化過程的產品。它們的地位源自這些自愿社團的原型,即教派的非常獨一無二的重要性。實際上,它們根植于那些最初的美國佬樂園之家――北大西洋諸州的教派。讓我們先回顧一下,美國民主中的普選(只限于白人!黑人與所有有色人種甚至今天在事實上仍無普選權),還有類似的“政教分離”,這些都只是最近才達到的成就,它們基本上發端于十九世紀。讓我們記住,在殖民地時代的新英格蘭中心區域,尤其在馬薩諸塞,州的完全公民資格的獲得的先決條件(此外也有些其它先決條件)是,獲得教會的完全成員地位。宗教圣會事實上決定著政治公民身份的被接納與否。(注13
這一決定所根據的是,某個人能否在最廣義上通過行為證明自己的宗教資格,就像在所有清教宗派中例子那樣。直到獨立戰爭前不久,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派才在較輕的意義上可以算是該州的主人。這已成為了的確的事實,不過從形式上說,他們還不是具有充分的政治公民身份者。只是依靠了大范圍的重新劃分選區,他們才成為政治上的主人。在教派圣會的充分參與權上,尤其在領取圣餐的權利上能夠被接納,這具有極重要的社會意義,由教派發展出的禁欲主義職業倫理在其最初階段,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而現在在教派中的社會意義是由這一倫理所哺育出來的。可以證明的是,在包括歐洲在內的任何一個地方,就如在上面所說的美國的個人經驗表明的那樣,禁欲主義教派的宗教虔敬幾個世紀中都是如此發揮影響的。
當關注這些新教教派的宗教背景時(注14),我們在書面檔案中發現這樣的事實(尤其是在整個十七世紀的貴格派和浸信會中),有罪的“世界之子”彼此在商業上不信任,但是他們在虔誠的宗教之義中產生信任,他們為此而一再發出歡呼。(注15)
所以,他們僅僅通過虔誠而委托并儲蓄他們的錢,他們也在這一范圍的店鋪中交易,因為在那兒、也只有在那兒,他們才有誠實和可靠的價格。如所知的,浸信會總是針對一個原則首先宣布提出這個價格策略。此外,貴格派也作了這一宣布,下面引用了一項材料,愛德華·伯恩施坦在當時提醒我們注意:
但是事實上,價格政策不僅僅和土地方面的法律有關,這些土地是那些堅守他們的諾言和神圣約定的最初成員所擁有的。在他們的商業利益中,這一特性對于他們來說都是實實在在的。在他們以社團的方式首先出現時,他們以作商人為苦差事,因為其他人由于不喜歡他們[宗教]儀式的特性,不愿意做他們店里的顧客。可是在短時間內,當他們把農村的商業也轉入手中時,外人大聲疾呼排斥他們。這一呼吁部分地源于在他們和其他人的所有商業協定都有嚴格的免稅權,也因為他們從不為他們所賣的商品去搞雙重價格。(注16)
對于那些通過奉獻和行為讓神悅納的人,神會保佑他們致富,這樣的觀點事實上在全世界都有。不過,新教教派有意識地將這一觀念和這種宗教行為聯系起來了,這從早期資本主義的這一原則可以看出:“誠實是最好的策略”,這一聯系不是僅在這些新教教派中有,但是只有在他們中間,這一特征才具有持續性和穩固性。
完整的典型資產階級倫理的來源范圍從普通人直到禁欲主義宗派和非國教徒的密會,它也是直到目前為止為美國的教派所實踐的倫理。例如循道宗有這樣的禁令:
(1) 禁止在買賣中討價還價;
(2) 禁止在關稅付清之前進行商品交易;
(3) 利息的收費率不得高于國家法律的規定;
(4) 禁止“聚斂土地財富”(指的是把投資資本轉化為“固定財富”);
(5) 在不能確保還債能力的情況下禁止借債;
(6) 禁止各種奢侈行為。
但是這里所討論的不僅僅是在細節上已經討論過的倫理問題(注17),那樣的話要返回禁欲主義宗派的早期開端。而首先在于,社會獎懲、紀律手段以及――一般的說來――新教教派的各個分支的整個組織基礎都要追溯到這些開端。它們在當代美國的繼承者乃是生活的宗教規則之派生物,這些派生物的社會功能的效率都是極高的。讓我們在此簡短地澄清這些教派的本質,還有它們的模式與功能之指向。
在新教當中,“信仰者的教會”這一原則首先明顯來于1523-24年間蘇黎世的洗禮派。(注18)這一原則將聚會只限于“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它意味著,這是由從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得到真正認可的人所組成的一個自愿團體。托馬斯·閔采爾否定嬰兒受洗;但是他沒有采取下一步驟,也即要求成人像嬰兒受洗一樣重新受洗(再洗禮主義)。蘇黎世的洗禮派追隨閔采爾,于1525年引入了成人洗禮(可能也包括再洗禮主義)。流動的旅行者和工匠是洗禮派運動的主要承擔者。在每一次受到鎮壓后,他們都將它帶到一個新的地方。這里我們不打算再細節上討論這些舊的洗禮派、門諾派、洗禮派和貴格派的自愿入世禁欲主義的個人形式,也不打算重新描述,每一種禁欲派別是如何一再落入同樣的路向的,包括加爾文派(注19)和循道會。
這種情況出現在要么是教會內部模范性的基督徒非國教徒密會中(虔敬派),要么是其他宗教上的“充分公民”(具有無謬誤的正當性)之群體中,他們是掌握著教會的主人。其他的成員僅僅屬于消極身份團體、或服從紀律的少數派基督徒(獨立派)。
在新教中,作為榮耀管理義務性組織的“教會”和作為宗教上合格者的自愿團體之“教派”,這兩種[不同的]結構原則在內外兩方面都有沖突,從茨溫利到Kuyper和St·cker,這一沖突幾個世紀來一直存在。我們在此僅僅希望考慮那些自愿主義原則的后果,這些原則在對其行為的影響上具有實踐上的重要性。此外,我們僅僅回顧這一事實,是圣餐純潔的決定性觀念,及因此對不合格者的排除,在那些沒有形成教派的派別中,也會產生一種處理教會事務的方式。尤其是預定論的清教徒,正是他們有效地由此達成了教派的紀律。(注20)
對基督教團體而言,圣餐的關鍵社會重要性在此是很明白的。對教派本身而言,神圣宗教團體純潔性的觀念在其最初時期,還是深具決定性的。(注21)很快的,第一個穩定的自愿主義者,布朗恩(Browne)在其“迫切宗教改革論(Treatise of Reformation without tarying for anie)”(可能是1852年)中強調,之所以在圣餐上要對“邪惡之人”維持宗教團體之壓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對主教制度和長老制度的拒絕。(注22)長老會徒勞無益地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在伊麗莎白時代(Wandworth會議),這已經成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注23)
有關誰應決定從圣餐中被排除者,這在英國革命期間的國會中是一個不斷出現的重要問題。一開始(1645)由執事(ministers)和長老,即平信徒自由決定這一議題。國會試圖處置這些事關開除的議案;所有其它的議案都是依靠議會而做出的。這被稱為“國家全能主義”(Erastianism),威斯敏斯特會議(Westminster Assembly)對此表達了尖銳抗議。
獨立派黨人取得優勢,因為除了得到認可的本地居民外,它只接納屬于宗教團體的人。只有得到合格的成員的介紹,外來聚會團體的成員才會被接納。資格證明書(介紹信)也在十七世紀出現了,它是在從一地往另一地或旅行時被授予的。(注24)在官方教會內部,巴克斯特的非國教徒密會(協會)于1657年被引入十六個縣,它們被設立成一種自愿性的審查機構。這可以讓執事更容易鑒別合資格者,并把那些名聲不好的人從圣餐中排除。(注25)威斯敏斯特會議中的“五抗議兄弟會”(five dissenting brethren)――這是居住在荷蘭的上層階級的避難所――也是如此,他們提出允許在教區旁邊存在由自愿者組成的圣會,并賦予他們票選宗教大會代表的權利。新英格蘭的全部教會史都充滿了圍繞這類事情的沖突:誰能被圣禮所接納(為一個主教,這是一個例子);未被接納者的孩子能否受洗(注26);還有在什么情況下后者可以被接納,及諸如此類的問題。困難在于,那些高貴的人不僅要被允許接受圣餐,而且還不得不接受它。(注27)所以,如果信仰者自己懷疑自身的價值,并遠離圣餐的話,這一決定本身不會消除他的罪。(注28)另一方面,為了能保持純潔,要讓那些無資格者、尤其是應受指責者(注29)遠離宗教聚會,圣會也是負有聯合責任的。所以通過一個負有榮耀的高尚執事,聚會團體對于圣事的管理是負有聯合且特別的責任的。這樣,教會章程最初的問題又重新出現了。巴克斯特做了折中的提議,在緊急情況下,來自不合格執事(即其行為是有問題的)的圣事應當被接受,但他試圖調和的做法并無成效。(注30)
[在這個問題上]在早期基督教時代,古代的多納圖派持個人卡里斯馬的原則,它和那種把教會視為管理恩典的機構的原則(注31)是截然對立的。通過教牧者的character indelebilis(不可損毀的完整性),在大公教會中激進地建立起了恩典制度化的原則,在宗教改革后的官方教會也是如此。獨立派的立場是激烈且不容妥協的,它們是建基于把圣會當作一個整體的宗教責任上。除了兄弟情誼,執事的德行也成為宗教聚會所考慮的。在此顯示了這些事情是怎樣通過其原則而成立的。眾所周知,荷蘭的Kuyper分裂派在最近幾十年里曾有深遠的政治影響。它源于下面的形式:為了抗議荷蘭國教會(Herfomde Kerd)的大宗教會政府(Synodal church government)的宣言,一家阿姆斯特丹教會的一幫長老,當然是平信徒,以首席執事Kuyper(他也是一普通的平信徒長老)為首,拒絕給聚會之外的布道者給予資格證書,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這些外部的布道者是不合格者或不信者。(注32)就實質上說,十六世紀的長老會與獨立派確實是互有敵意的;最重要的后果是由圣會的聯合責任所肇端的。與自愿原則幾乎一致的是,合格者是被聚會團體所自由接納的,當然僅限于合資格者,我們發現地方圣事團體的支配原則就是如此。通過對個人的調查和熟知,只有本地宗教共同體可以裁決一個成員是否合格。但是跨地方團體的教會政府就不能如此,不管此政府的管理在選舉上有多么自由。要是成員的數量被限制的話,地方圣會可以進行挑選。所以原則上來說,這只適合于相當小規模的圣會。(注33)
要是團體太大了,要么就像虔敬派那樣形成秘密集會,要么反過來,這些成員像循道宗那樣被組織起來,成為教會紀律的承擔者。(注34)這些自治圣會所具有的超常嚴格紀律(注35)構成了第三條原則。這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這和圣事團體的純潔性旨趣有關(如貴格派中,和祈禱者團體之純潔性旨趣有關)。實際上,禁欲主義宗派的紀律比任何教會的紀律都要嚴厲得多。在這方面,教派可與僧侶序階相比。教派紀律也和僧侶的紀律很相似,因為它建立了見習原則。(注36)與那些官方新教教會不同的是,由于道德犯規而被開除的人通常被拒絕與其他成員交談。故而教派對他們是實行絕對排斥的,包括在商業生活中。有時候,除非萬不得已,教派是避免與并非自己兄弟的人發生聯系的。(注37)而且教派將這種超級的紀律權置于了平信徒之手。在上帝面前,沒有什么精神權威可以承擔團體的聯合責任。甚至在長老會中,平信徒長者的分量也是很重的。不過,獨立派、甚至還有浸信會則不懈地與神學家的權威或統治作斗爭。(注38)正是由此,這一斗爭自然導致了平信徒成員的職事化,他們通過自我管理、警告、甚至可能開除來發揮道德控制的功能。(注39)教會平信徒的統治也部分地表現在他們對自己布道之自由(預言的自由)的尋求上。(注40)為了讓這一訴求合法化,向早期教會團體的情況作了參考。這一訴求不僅對于路德派的教牧官職(pastoral office)觀念是離經叛道的,對于長老派的神命(God’s order)觀念也是如此。平信徒的統治還部分地表現為,他們反對任何職業神學家和牧師。唯一應得到認可的只有卡里斯馬,而不是訓練和官職。(注41)
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下)
貴格派則堅持這樣的原則,在宗教聚會中任何人都可以發言,不過他只能談他被圣靈的感動。所以那里根本沒有職業執事。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可以確信的是,直到今天,沒有任何地方因此產生過大不了的后果。正式版的“傳奇”是這樣說的,那些在聚會侍奉時被圣靈所特別蒙納的成員在聚會的時候,坐在一圣會對面的特別長凳上。在深深的靜默中,等待圣靈的人們掌控著他們中的一個(或聚會的某些其他成員)。但是在一家賓夕法尼亞學院的侍奉中,與我的愿望不幸的相反的是,圣靈沒有控制那位坐在凳子上的樸素而美麗的女士――她的卡里斯馬受到高度贊揚。相反,大家一致同意圣靈控制了一位勇敢的學院圖書管理員,他就“圣徒”這個概念作了一通很博學的演講。
可以肯定的是,其它教派并沒有得出這樣激進的結論,至少沒有想要一勞永逸地如此。不過雖然如此,執事要不是作為“雇員”而積極活動的話(注42),也會為了自愿的光榮捐獻而侍奉。(注43)其侍奉可能還是一種次級的職務,并僅僅是從事其費用的重新募集(注44);[不然的話]要么他被解職;要么就是作為一種巡回布道(注45)的傳教組織,僅僅偶爾沿著相同的路線工作,如在循道宗就是如此。(注46)只要(傳統意義上的)官職和相關的神學資格得到維持(注47),這種技術就會被視為是一種純粹技術性和專門性的特權。不過,真正決定性的要素是榮耀狀態下的卡里斯馬,而其權力機構就通過調整自己來辨別它們。
權力機構,如克倫威爾時代的triers(控制宗教資格許可證的地方實體)和ejectors(執事紀律之官職)(注48),必須要檢查執事侍奉的適當性。權力機構的卡里斯馬性格被認為是以這樣的特征保持著――它與團體自身成員的卡里斯馬特征的保持方式相同;如克倫威爾的圣徒軍只允許宗教上合格的人進入他們的圣餐,所以如果一個軍官出自不符他們宗教資格圣事之團體的話,克倫威爾的士兵就會拒絕作戰。(注49)
在教派成員中,早期基督教兄弟之情的精神仍內在地隨處可見,至少在早期浸信會和其衍生派別中是如此;至少也會對此做出要求。(注50)在某些宗派中,打官司被當作一種禁忌。(注51)除非萬不得已,相互幫助是一種義務。(注52)自然,與非成員間的商業交易不會遭到干涉(除在極端派別團體中會偶爾為之)。
不過從他們的自我理解來看,他們是更偏好于兄弟之情的。(注53)從一開始,人們看到許可證制度就是如此(與成員資格及其行為有關)(注54),它在其成員遷移到另一地方的時候被授予。貴格派的慈善事業高度發展,由于其所承擔的這些負擔的緣故,他們[對此]宣傳的勁頭也就減弱了。圣會的凝聚力很強,所以它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是新英格蘭定居者之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與南方不同的是,新英格蘭的居民點普遍密集,并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的城市化特征。(注55)
很明顯,在所有這些方面,美國教派和類似教派的組織的現代功能被揭示出來了,就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那樣,它們是曾經在所有禁欲主義宗派和秘密集會中廣為流行的,而其現代功就是那些情況的直接派生物、剩余物和積淀物。今天它們也正在走向衰敗。從一開始,這些教派主義者就明顯有一種非常排他性的“孤芳自賞”(pride in caste)。(注56)
現在我們來看,在這整個發展過程中,是哪一部分對我們的問題過去和現在具有實際的決定性作用呢?在中世紀,被逐出教會也會有政治和民事上的后果。而且就形式上而言,在自由度上比教派要更為苛刻。此外,在中世紀只有基督徒才是充分的公民。在中世紀,也有可能通過教會的紀律權力來反對一個不還債的主教,舒爾特(Aloys Schulte)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這一原因使得主教比世俗諸侯具有更高的信用度。與此相似,一個普魯士副官如果不能清償債務,那就會被解職,正是這一事實也使得他能夠擁有較高信用度。德國學生的友情也與此相同。在中世紀,教會所擁有的口頭悔改和紀律上權力也是如此,它可使教會紀律有效發揮作用。最后,通過訴諸法律,[債務上的]誓言也可以保證把債務人革出教門。
盡管如此,在所有這些例子中,與那些新教禁欲主義所哺育或壓逼出來的行為模式相比,經由這些條件和手段所得到贊同或反對的行為模式與前者還是總體上不同的。我們可以以副官、或友誼會的學生、也可能是主教作為例子,信用度的提高肯定并不依靠與商業行為相應的個人資質的培養;直接看看下面的評論:即便這三個例子的影響是相同的,它們也是一非常不同的方式發生作用。首先,像路德宗那樣的中世紀教會紀律是處于執事官員的掌控下起作用的;第二,通過這些威權式的手段,這一紀律才得以最有效的發揮作用;第三,它只是對具體的個人行為實施獎懲的。首先,至少部分的及經常是全部的,清教徒與教派的教會紀律是授予平信徒之手的。第二,它要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第三,它培養或選擇了不同的品德,如果人們希望如此的話。最后一點是最重要的。
為了能夠進入團體的圈子里,教派(或非國教徒密會)的成員必須有某種品德。這些品德對于理性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重要的,這在第一篇文章里也指出了。(注57)為了能呆在這個圈子里,成員必須要一再證明,他賦有這些品德。他持續不斷地培養這些品德。因為就像上天對他的賜福,他所處的全部社會地位現在都要依靠他對自己信仰的“證明”。在減輕一個人的罪的手段上,天主教的懺悔是反復地來自內心的巨大壓力,而教派成員則面對這種壓力而不斷地加以控制。關于中世紀的正統和異端宗教團體是如何成為新教禁欲主義派別的先驅的,這些在此就不想討論了。
根據各種情況來看,通過保持其在團體的圈子里地位而來培養自身資質的做法是最有力的了。所以,教派的穩定而至高無上的倫理紀律是和權威主義的教會紀律相聯系的,而理性化的培養與選擇[方式]是和秩序與禁忌相聯系的。
幾乎所有的其它情況也表明,清教教派是禁欲主義的內向形式的最不同尋常的承擔者。此外,他們是最穩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唯一穩固的普世大公教會的反對者,他們是恩典管理的義務性組織。在這些資質的培養上,清教教派把關于社會地位的個人利益置于了強有力的地位上。所以,從各個方面說,個人的動機與自身利益也在產生和維持“中產階級”上發揮著作用。清教倫理[體現在]所有它的分支中。究其深遠的及無與倫比影響力而言,這絕對是決定性的。
需要一再指出,不是宗教的倫理教義,而是它的倫理行為方式在發揮著獎懲作用。(注58)這種獎懲是通過救贖的個別之善的條件和形式而發揮作用的。并且在社會學意義上,這樣的行為構成了一個人的具體“倫理”。某種程度上,對清教而言,那種行為是一種生活的系統化和理性化的路向,它為現代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在救贖意義上,這些獎懲是在上帝面前來證明自己的(在所有清教派別中都可以發現這一特征),而就清教教派內的社會地位而言,它是在控制著自己的人面前來“證明”自己的。這兩個方面互為補充,又在同一方向上運作:它們有助于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傳播。它的具體精神氣質是:現代布爾喬亞中產階級的精神氣質。就現代“個人主義”而言,禁欲主義宗派和秘密集會構成了其最重要的歷史基礎之一。它們激進地突破了父權制和權威主義的限度(注59),此外它們還強調了順服上帝而不是人,這些尤其重要。
最后,為了理解這些倫理影響的本質,需要作出一個比較性的評論。在中世紀的行會中,一直有對其成員的一般倫理標準的控制,它與禁欲主義清教教派紀律的運作方式相似。(注60)但是行會和教派對于個人經濟行為的影響就必然不同,這一點是很明顯的。行會把同職業者聯合在一起;這樣它聯合了不同的競爭者。它這樣做的目的在于,限制競爭,并理性地尋求通過競爭而得到的利潤。行會培訓出了“民事”素質,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中產階級“理性主義”的承擔者(對此不想予細節上討論)。行會是通過“永久的政策”及傳統主義而完成這一點的。
另一方面,通過將倫理上合資格的信仰追隨者加以培養和選擇的做法,教派將人整合起來了。他們的成員資格并不是基于學徒資格,也不是基于和職業技術有關的家庭關系。僅僅是在形式正義和條理化的禁欲主義上,教派控制和指導著其成員的行為。它與物質性永久目標無關,后者被認為是有礙于對利潤的理性尋求的發展的。行會成員的資本主義成功逐漸損害了行會的精神(在英法都是如此),所以資本主義的成功也[反過來]受到了阻礙。但是只要法律許可,教會兄弟的資本主義成功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和榮耀,并且也提高了教派的威望和宣傳機會。所以這樣的成功是受歡迎的,這在前面業已指出了。行會的自由勞動力組織在其西方中世紀的形式中,當然不僅是一種阻礙(這和他們的本意也相違),而且也是勞動力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先決條件,這一點或許也是必不可少的。(注61)但是當然,行會不能促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只有禁欲主義宗派的條理化生活方式才能賦予它合法性,并且也給現代資本主義氣質的經濟“個人主義”沖動蒙上一層光環。“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Hans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in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s of Capitalism, intro & trans by Stephen Kalber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p. 127-47.
【注釋】:
1 這篇文章有個唯一的譯本,就是本書中的,譯者為Hans H. Gerth和C. Wright Mills。為了與《新教倫理》一書在術語上統一,少數用語作了修改。書目方面的信息見此文p. 263的第一個腳注。
2 現在有早期文章的兩個譯本,這里所提供的版本是韋伯在1920年擴展的。此外還加了大量的注腳。
3 當然,更早還有托克威爾強調美國社會的這一發達的能力。不過,就組建團體的傾向(這一點與美國有“多數人暴政”的傾向是相對立的)而言,他的解釋在許多方面與韋伯有所不同;托克威爾強調平等主義、商業利益以及個人利益,而韋伯則指向禁欲主義新教的宗教遺產。
4 就某個人的社會地位而言,韋伯極端強調進入一個社區的教會和俱樂部的重要性(例如Rotary, Lion等),這會導致把美國描述為一種“好的封建主義”的社會。
5 在《法蘭克福時報》(Eastern 1906)出了一篇文章新的、擴充了的綱要,后來又在《基督教世界》(1906,pp. 558ff., 557ff.)作了一些擴充,題目為“教會與教派”。我一再將此文作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補充。現在又將它重寫,其原因在于,教派這個概念是由特洛爾奇在他的《基督教會的社會學說》中加以徹底闡釋和運用的,我自己也使用了它(將它與“教會”的觀念相對),并且也很喜歡這個概念。所以,概念上的討論盡管在《新教倫理》(pp. 221, note 200)中已指出了其必要性,但在此還是輕易省略了。這篇文章只收入了那篇文章顯而易見的補充材料。
6 考慮到天主教徒選票的重要性,還有對告解學校(confessional school)的資助;這一原則常常只是理論上的。
7 在此對其在細節上并無興趣。可以參看“美國教會史系列”的各卷,這一著作質量參差不齊。
8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僅美國最高法院開庭的時候,就是每一個黨派的傳統中,都有這種公開的祈禱,它們構成了一套煩人的儀式。
9 在一所東部大學中教閃米特語的助教告訴我,他很遺憾沒有成為“講席擁有者”(master of the chair),所以他打算重返商界。當問這樣做有什么好處時,回答是:作一個流動商人或貨主,他能夠充分表現自己,使自己得到令人尊敬的名聲。他能夠擊敗任何競爭者,并使自己的價值得到最好的體現。
10 在美國,這些方面所表現出的“偽善”和傳統的投機主義并不比德國更強,畢竟,在德國,一個“沒有宗教歸屬或取向的”官員或公仆也是不可能的。有一位柏林的(雅利安人!)市長大人沒有得到官方確認,就是因為他沒有讓自己的一個孩子受洗。這些傳統的“偽善”有不同的表現:德國的官員職位,美國的商業機會。
11 學生友誼,與“希臘字社團”相對。
12 不過前面也提到過了。失去德國國籍很關鍵的一點在于,(在學校或之后)進入一個美國俱樂部。
13 在往新英格蘭移民期間,這些宗教聚會組織經常是先于政治社會而存在的。(其以Pilgrim Fathers[注-指最早到美國的宗教逃亡者與教士]協議的形式而廣為人知)故而,1619年多爾切斯特(Dorchester)移民首先這樣做了,他們在移民之前組織了一個教會,由此把自己組織起來了,他們選出了牧師和教師。在馬薩諸塞殖民地,教會在形式上被認可為徹底自治的團體,不過另一方面,只有屬于其者和具有成員資格者才能成為公民。與此相同,在紐黑文教會(在它在康涅狄格州被組織起來之前,鄉鎮是有義務維持教會的)一開始也如此,教會成員資格和善行(意味著可領圣餐)也是成為公民的先決條件。(這也是獨立派以嚴格的紀律來表達對長老派的不滿)這就立即意味著更為寬松的實踐,因為在紐黑文的教會被整合起來之后,這種資格的限定是比較寬泛的,它包括那些宗教上不那么令人討厭的個人。甚至在17世紀,在緬因和新罕布什爾州的整合上,馬薩諸塞不得不放寬了對[享有]政治權利之宗教資格的嚴厲限制。在教會成員資格的問題上,也不得不作出了這樣的承諾,最有名者就是1657年的Half-way Covenant(注-指某些教友不屬于教會但是也能參與教會事務)。此外,凡是不能證明自己獲得重生的人,仍然可以獲得成員資格上的接納。但是到18世紀初,他們才可以被聚會所接納。
14 可以列舉舊文獻中的一些資料(它們在德國不太為人所知)。Vedde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aptists (2nd ed. London, 1897)提供了浸禮會歷史的梗概;關于Hanserd Knollys:Culross, Hanserd Knollys, edited by P. Gould (London, 1891), vol. II(浸禮會手冊卷)。
關于再洗禮派的歷史有:E. B. Bax, Rise and Fall of the Anabaptists (New York, 1902);關于Smyth:Henry M. Dexter, The True Story of John Smyth, the Re-Baptist (Boston, 1881), 這是他本人和同時代人的敘述;一直以來都被引用的關于Hanserd Knollys社團的重要出版物(這是由J. Hadden為社團所付印的,Castle Street, Finsbury, 1846-54);還有官方的文獻見于The Baptist Church Manual by J.Newton Brown, D.D. (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shing Society, 30 S. Arch Street)。關于貴格派,除了Sharpless所引的著作,還有:A. C. Applegarth, The Quarkers in Pennsylvania, series X, vol. VIII, IX,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與政治科學研究系列;G. Lorimer, Baptists in History (New York, 1902); J. A. Seiss, Baptist System Examined (Lutheran Publication Society, 1902)。
關于新英格蘭(除Doyle外)的有:馬薩諸塞歷史匯編;此外還有Weede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1620-1789, 2 vols. Danial W. Howe, The Puritan Republic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關于舊的長老派之“誓約”觀念的發展,它的教會紀律,還有其與官方教會的關系,及與公理會和其他教派的關系,可見:Burrage, The Church Covenant Idea (1904)與The Early English Dissenters (1912);此外還有,W. M. Macphail,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918);J. Brown, The English Puritans (1910);Usher, The Presbyterian Movement, 1584-89 (Com. Soc., 1905)是重要的文獻。我們此處所給出的乃是與我們[研究]相關的非常隨機性的列舉。
15 前面提到的Bunyan有一個“Mr. Money-Love”的看法,即認為人們會為了獲得財富而變得虔誠,尤其是為了得到更多的贊助,這在十七世紀被認為是非常理所當然的;對于人們為什么會變得虔誠,這應是無關緊要的。(Pilgrim’s Progress, Tauchnitz ed., p. 114)
16 Thomas Clarkson, Portraiture of the Christian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London, 1867), p. 276.第三版(首版出于1830年左右)
17 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18 資料來源是茨溫利的論述:Füssli I, p. 228, cf. also pp. 243, 353, 263; Elenchus contra catabaptistas, Werke III, pp. 357, 362. 在其聚會中,茨溫利很典型地遇到了反對嬰兒受洗論者的困擾。這些人認為根據圣經,洗禮派的“分離”(因而也是意志論者)是令人反感的。布朗派在1603年向詹姆士國王進行了請愿,要求將所有“邪惡的撒謊者”從教會中驅逐出去,只接受“信仰者”和他們的孩子。但是長老會(大約)于1584年的教會統治的備忘錄(其原件第一次發表于A . F. Scott Pearson在海德堡的Ph. D論文,1912)則在第37款要求,只有服從紀律的人,或是(以別的方式表達其見證)者才可以被聚會所接納。
19 教派的自愿主義原則在本質上是有爭議的,它在邏輯上是遵循改革派教會(加爾文主義者)基于ecclesia pira的要求而來的。就如教派紀律所反對的那樣,這一教義原則現代在Kuyper(后來以第一執事而出名)那里是非常明顯的。他最后的一篇文章的標題就特別明顯地顯示了這一立場:Separatie en doleantie (Amsterdam, 1890)。他將此問題歸因于在非天主教基督教中,沒有永不謬誤的教義機構。這一教義斷言,看得見的教會的“軀體”并非舊的改革派教會之“圣體”(Corpus Christi),不過它在時間和空間上一定是保持分裂的,人性的弱點也一定保持了其對此的特性。一個可見的教會就信眾、及基督賦予他們的權威而言,其僅僅源于“一種意志的行為”(an act of will)。所以,抗議宗教會(potestas ecclesiastica)既不屬于基督本身,也不屬于執事(ministri),而僅僅屬于信眾團體。(在此Kuyper跟隨了Vo?t的立場)更大的共同體源于聚會者基于法律和自愿的聯合。
不過,這種聯合體一定是一種宗教的義務。根據羅馬的法令,這種聯合體是被拒絕的,因為教會成員只被允許出于他所處的本地社區的教區之中,他僅僅是一個eo ipso成員。浸禮只是賦予了他一種是純粹消極而不完全的角色(membrum incompletum),而沒有賦予他任何權利。在法律意義上,不是浸禮,而僅僅是belijdenis en stipulatie(信仰的歸依與善良意志的表白)授予了團體的成員資格。成員資格本身是要服從于教會紀律的(disciplina ecclesiae這也是Vo?t的立場)。教會法被相信是用來對付看得見的教會的那些人為的規則的,而那些規則,雖然和上帝的秩序相聯系,但并不代表上帝的秩序本身。(cf. Vo?t Pol. Eccles. vol. , pp. I and II)
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改革派教會中真正的根本法的獨立派因素,它們暗示出聚會團體(因而也是平信徒的)在接收新成員方面的一種積極性參與形式。(Von Rieker將這些法描述得很好)整個聚會團體的合作成員也構成了在新英格蘭的布朗獨立派(Brownist Independents)的重要一環。他們堅持這些立場,并強烈的反對冉森派(Johnsonist)的成功發展,后者堅持教會要受“長老”的統治。只有“改過重生者”才會被接納(根據Baillie,這些人是“四十個人才出一個的”)。在十九世紀,蘇格蘭獨立派的教會理論也差不多這樣看:只有通過特殊的方式才能獲得教會的接納(Sack, loc. cit.)。不過,Kuyper的教會理論在本質上當然并非是“會眾制”(congregationalist)的。
根據Kuyper的看法,個體的聚會在宗教上是有義務向作為整體的教會靠攏并屬于它的。在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個合法的教會。只有當“抗議”失敗時,這種歸屬的義務才會消失,分離的義務才會出現,也就是說,必須通過積極的抗議、消極的破壞等努力,以使得不好的教會得到改善(doleeren意為抗議,從技術上來說出現于17世紀)。最后,如果所有的努力都被證明無效的話,強制的做法興起,而分離也就成為一種義務。當然,如果是那樣的話,一個獨立派的憲章也是有必要的,因為在教會中沒有了“主題”,并且也因為信眾在本質上擁有神授的地位。革命可以是對神的一種義務(Kuyper, gekomen, pp. 30-31)。Kuyper(像Vo?t一樣)采納了一種久的獨立立場,即認為只有那些通過參與圣餐而被接納者,才是教會的真正成員。只有后者才能夠在浸禮期間承擔其孩子的委托權利。在神學意義上,一個信仰者就是一個內在的歸依者;而在法律意義上,一個信仰者僅僅是一個被接納參加圣餐儀式者。
20 對于Kuyper來說最基本的前提是,不把不信者的宗教聚會團體清除就是一種罪。(Dreigend Conflict, 1886, p. 41;參考Cor.11:26-27, 29; 1 Tim. 5: 22; Apoc. 18: 4.)但另方一方面在他看來,教會永遠無法判斷“在上帝面前”的恩典的狀態――與“Labadists”相對(屬激進的虔敬派)。不過就圣餐的接納而言,只有信仰和行為才是決定性的。十六、七世紀時荷蘭宗教會議在處理如何參加圣餐的先決條件上爭論不休。例如,1574年荷蘭南部的總教會議同意,如果沒有有組織的聚會的話,就不應當發放圣餐。長老與執事要小心注意,不讓沒有資格的人獲得接納。1575年的鹿特丹會議作出結論,所有在生活中犯有明顯過錯者不應被接納。(決定接納與否的不僅是牧師,還有長老們,那些提出這些反對意見的團體幾乎總是對牧師們更為寬松的政策持反對立場。如可參見Reitsma所引的例子[vol. II, p. 231])
圣餐接納的問題包括了以下的方面:關于一個再洗禮派教徒的丈夫能否被圣餐接納,在1619年于萊頓的宗教大會作出了決議,見第114款;倫巴第族的仆人能否獲得接納,1595年在Deventer的省級會議上作了決議,見第24款;那些宣布破產者能否接納,見1599年在Alkmaar的會議第2款,還有1605年會議的地28款;還有關于已經建立了協議的人也應被接納,1618年Enkhuizen的北荷蘭大會,Grav. Class. Amstel.第16條。后一種情況在以下情況是得到肯定回答的,只要宗教法院(consistorium)發現,[候選人]具有足夠的財產,并斷定他能保證債務人和家人都有足夠的衣食供應,那么就可以了。尤其是當債權人自己也對此協議很滿意,且債務人在未能履行義務的情況下進行悔罪,那就更是如此。有關倫巴第人的非準入資格,可見上面。為了避免爭執,配偶是被排除在外的,Reitsma III, p. 91。準入的另一個先決條件是,各個派別的法律爭執得到和解。對于長久的爭執,他們必須拿到聚會之外去[解決]。那些洗清了名譽的損害且對此一直有興趣者,也可以獲得有條件的接納。見同上,p. 176。
很可能是加爾文在法國移民的斯特拉斯堡聚會團體中第一個要求,要把那些其行為沒有令人滿意地通過考試的人從圣餐中排除出去。(不過后來不是該團體,而是執事大臣作出了該決定)根據真正的加爾文教義(Inst. Chr. Rel. IV, chap. 12, p. 4),除名的做法在法律上只能被運用于責難。(如在前述場所,除名被認為是頒布一項神圣判決)但是在同一地方(cf. p. 5),它也被視為一種“改進”的手段。
今天在美國,至少在都市地區,在浸信會中正式的除名還是很少見的。在實踐上,實行的是“退出”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某人的名字被簡單地且謹慎地從記錄當中劃掉。不過,在教派和獨立派當中,平信徒已經是紀律的典型承擔者了;而在最初的加爾文主義的長老派教會中,紀律是明顯而系統性的試圖要統治國家和教會。但是,在教會治理的階層和高級官員的問題上,甚至1854年英格蘭長老派的“備忘錄”(p. 14, note 2)也提倡由平信徒長者和執事們來擔當。
長老們和聚會團體的關系在不同情況下是有所不同的。就像(長老派的)長期國會把從圣餐中開除的決定權轉交到(平信徒)長老之手一樣,新英格蘭地區1647年的Cambridge Platform也與此類似。但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蘇格蘭獨立派還是把錯誤行為的公告交付一個委員會處理。在該委員會作出通告后,整個團體才作出開除的決定,這是一種對所有個人的關連義務更為嚴格的立場。這在前述布朗派的告白中也有反映,它是于1603年提交給詹姆士一世的(Dexter, loc. cit., p. 303),而“冉森派”則認為(選舉出來的)長老的統治是符合圣經的。長老們甚至可以與團體的決議相對,而行使開除的權利(如對Ainsworth的分離事件)。想了解早期的英格蘭長老會中的相關情況,可參見在前面注解4中所引的文獻,還有注解7中所引Pearson的博士論文。
21 順便說一下,荷蘭的虔敬派也相信這一原則。例如,Lodensteijn持這樣的觀點,人們必須同沒有重生的人相處;后者對前者來說很明顯是無重生跡象者。他甚至反對給孩子們談主禱(Lord’s Prayer),因為他們還沒有變成“主的孩子”。在尼德蘭,Kahler有時候還會見到這樣的觀點:重生者根本不會犯罪。在較小的中產階級下層群體中,確實可以見到正統的加爾文主義教義和令人吃驚的圣經知識。由于不相信神學教育和面對1852年的教會規定,正是正統派人士作出這樣的抱怨,平信徒在宗教大會中是缺乏充分的代表性的(除此之外還缺乏足夠嚴格的censura morum)。那時候德國正統的路德派教會還是不這樣看的。
22 轉引自Dexter, Congregationalism of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as Seen in its Literature (New York, 1880), p. 97.
23 伊麗莎白時代的英長老會希望認可英格蘭教會的39款規定(不過對34至36款保留,它們在此無關緊要)。
24 在十七世紀,從地方聚會團體中的非定居的浸信會眾所開出的介紹信是被圣餐接納的先決條件。非浸信會眾只有在經過團體的考察并得到認可后,才能被接納。(Hanserd Knollys Confession 1689年版的附錄,West Church, Pa., 1817)對于合資格的成員來說,參與圣餐是一種必需的義務。如果沒有加入到合法組織的本地聚會團體中,那就會被認為是分離主義。就帶有其他團體的必需的共同體而言,浸信會眾的觀點與Kuyper的看法(cf. above, note 8)相似。不過他們不承認有高于個別教會的任何司法權威。想了解訂立盟約者與早期英格蘭長老會眾的(介紹信),可見注解7和?中所引的文獻。
25 Shaw, Church History under the Commonwealth, vol. II, pp. 152-65; Gardiner, Commonwealth, vol. III, p. 231.
26 布朗派(Brownist)甚至在1603年向國王詹姆士對此請愿抗議。
27 例如,這一原理在1585年Edam的一個宗教會議的相似決議中得到表達。(見Reitsma系列,p. 139)
28 Baxter, Eccles. Dir., vol. II, p. 108在細節上討論了那些受到可疑的成員從聚會的圣餐中狼狽離去的場面(其根據是英格蘭教會的第25款)。
29 預定論的教義在此得到最純粹的表達。那些受到指責的孩子在其得到可靠證明后是否可以接受洗禮呢,此一表達對于這一問題是有著無比的關系和實踐重要性的。不過,預定論教義的實踐重要性還是一再受到不公平的質疑。在阿姆斯特丹難民的四個團體中,有三個贊同接納這些孩子們(十七世紀初);但是在新英格蘭,只有1657年的“Half-way Covenant”在此問題上作了放松。關于荷蘭的情況,見注解9。
30 Loc. cit. vol. II, p. 110.
31 還在十七世紀初,對非國教徒聚會的禁令就已經在荷蘭導致了一場普遍的“文化戰爭”(Kulturkampf)。伊麗莎白對非國教徒的聚會義非常粗暴的手法加以反對(在1593年加以罰款的威脅)。在此后面的[真正]原因是禁欲主義者宗教上的反權威主義性格,或者更確切的說,在宗教和世俗權威之間有競爭性關系(Cartwright曾明確下令,即使是親王也得以被除名)。事實上,蘇格蘭的例子就必然有威懾性的影響,那里的長老派教會紀律之階級土壤和神職人員統治站在了國王的對立面。
32 為了避開正統牧師的宗教壓力,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公民吸取了自己的教訓,曾把他們的孩子送到相鄰的聚會團體中去。阿姆斯特丹團體的Kerkraad教會理事會(于1886年)拒絕承認由這些執事所制定的成員之道德行為的資格證書。這些成員被從圣餐中排除,因為團體必須要保持其純潔性,也因為必須服從主(而非人)。當宗教大會委員會贊同對這種分離行為否定的做法時,教會理事會拒絕服從和采納新規則。根據后者,教會理事會的拒絕給了自己超越于教會之上的獨一無二的授職權。這就拒絕了帶有宗教會議的社區,并將(平信徒)長老們架空了,T. Rutgers與Kuyger為Nieuwe Kerk[New Church]之詭計所困,盡管前者的看護人中也有后者。(Cf. Hogerfeil, De kerkelijke strijd te Amsterdam, 1886,此外還有前面提及的Kuyger之著作)
在1820年代,預定論運動就已經開始了,領導者為Bilderdijk和他的弟子Issac da Costa及Abraham Capadose(兩個受洗的猶太人)。(因為預定論的教義拒絕某些東西,例如像拒絕種痘那樣拒絕把廢除黑奴作為對羅德州事務的干涉)他們滿懷激情地為放松教會紀律而戰斗,并對不合格者準入圣事。這一運動導致了[教派]分離。1840年,阿姆斯特丹的“Afgeschiedenen gereformeerten Geemeente”(分離的改革派團體)接納了Dorderecht Canouns,并拒絕了任何一種“在教會之內或之上”的支配形式。Groen van Prinsterer是Bilderdijk的門徒之一。
33 1611年在“Amsterdam Confession”中建立了古典的規則陳述(Publ. of the Hanserd Knollys Society, vol. X)。故而,第16款這樣規定,“每一教會與團體的成員都應該相互認識……所以一個教會不應建立在數量的基礎上,使各成員彼此不知悉。”故而在最新的情況中,任何宗教大會的規則與任何中心教會的權威之建立都被視為原則上的叛教。這在馬薩諸塞州出現了,而且就像克倫威爾治下的英格蘭。這些規則是議會在1641年建立起來的,在那時它們允許每一個團體為自己準備一個傳統的執事,并組織演講。這一手段導致了浸信會成員的流失和激進的獨立派的出現。早期的長老會Dedham協議(由Usher發表)也預示了這一點,肯定對個別團體(在那時事實上最可能是個別執事)是教會紀律的承擔者。在1582年10月22日的協議中明顯的是以投票表決是否接納,“沒有全體的普遍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帶入到任一群體中。”不過早在1586年,這些接受了公理會原則的清教徒就宣布,他們反對布朗派成員的加入。
34 循道宗的“班”――以靈魂的合作治療為基礎――乃是整個自制的脊梁骨。每十二人就組成一“班”。班的領導者在每周都要拜訪每個成員,要么在家里,要么在班聚會中,在此他們通常要對罪作出普遍的懺悔。領導者要對每一個成員的行為作出記錄。在其他情況下,這些書面記錄將決定那些離開了本地社區的成員的書面資格。到目前為止,很長時間里,這種組織在每個地方都一直處于瓦解狀態,包括美國。從前引Dedham協議可以看出,早期的清教主義之紀律就是此種方式運作,據此在非國教徒聚會中“如果有任何事情被弟兄看到或觀察到”,要給予“警告”。
35 在路德派的地盤,尤其是德國,教會紀律不是糟糕地毫無發展,就是在早期就已經被徹底耽誤了。在德國的改革派教會里,教會紀律也是只有微不足道的影響,只有Julich-Cleve和其它萊茵地區例外。這要歸因于路德派外部環境的影響,還有在國家權力和競爭性、自主性等級力量之間的相互妒忌。這種妒忌無處不在,不過國家在德國過去還是一直有無上的權力。(雖然如此,教會紀律直到十九世紀才建立起來。最近的一次除名發生在1855年的諸侯領地上。但是,1563年的教會規則從早期開始,就一直以一種實際上是國家全能主義的方式被操控著。) 只有門諾派和后來的虔敬派產生了有效的紀律約束手段,即相關的組織。(對門諾來說,一個“可見的教會”僅僅存在于有教會紀律存在的地方。由于不當行為和混亂的婚姻會造成除名,這在這些紀律中是一個自明的要素。Rynsburg Collegiants沒有什么教理,只是根據“行為”來判斷。)在胡格諾派(Huguenots)之中,教會紀律本身是非常嚴厲的,不過通過不可避免的高貴性的考慮(這在政治上是必不可少的),嚴厲的紀律被一再放松。
清教教會紀律在英格蘭的擁護者尤其見于資產階級化的中等階級中,即如,倫敦市的中等階級。城市不擔心神職人員的統治,反而希望把教會紀律作為大眾生活的一種方式。工匠階層也非常支持教會紀律。政治權威則是教會紀律的反對者。故而在英格蘭的反對者也包括了議會。瞟一下每一個文件就可以看到,在此有影響的因素并非“階級利益”,而是基本的宗教利益與理解,此外還有政治的。不僅在新英格蘭,而其在歐洲的真正的清教教會都是出名的嚴苛。在克倫威爾的major-generals和委員中,為了推行教會紀律,他的代表們提出要驅逐所有“懶散、荒淫和瀆神的人”,這樣的動議被一再地提出。
在循道宗中,新手在受罰期間推出是被允許的,無需更多糾纏。老資格的成員的退出要經由一個委員會的調查之后才行。胡格諾派(它很長時間實際上都是一個“教派”)的教會紀律在宗教會議的協議中可以見到。在其他方面,這些東西顯示出可以擔保沒有貨物摻假和商業欺詐行為。(見Sixth Synod,Avert. Gen. XIV)故而反奢侈的法律是針對財政普遍比較緊的情況而實行的(fiscus是一個暴君),見Sixth Synod, cas de conc. dec, XIV;關于高利貸,見同上XV(cf. Second Synod, Gen. 17; Eleventh Synod, Gen. 42)。到了十六世紀末,英國長老會眾在官方通信中被稱為“紀律主義者”。(引文見Pearson, loc. cit.)
36 幾乎在所有教派中,都有一段見習期。如在循道宗中,為期六個月。
37 在威斯敏斯特宗教大會上的五個(獨立派)“反對派兄弟”中的“Apologetical Narration”中,從那些“不堅定和形式上的基督徒”中分離出來的問題被置于首位。這首先意味著這只是一種自愿式的分離,而非一樁交易。但是羅賓遜,一位嚴厲的加爾文主義者和Dordrecht大會的擁護者(關于他見cf. Baxter, Congregationalism, p. 402),最初持這樣的觀點(后來有松動),獨立派分離主義者不一定要和其他人做社會交流(即便他們是被選舉出來的),這被認為是可以理解的。盡管如此,大部分教派都避免讓自己明顯地與這種紀律掛鉤,有些則明白地拒絕它,至少在原則上是如此。巴克斯特(Christian Directory, vol. II, p. 100之第二欄的底端)以為,如果不是本人而是家長與郊區牧師承擔了責任的話,那么這個人就等于默許了與一個無信仰的人共禱。不過,這是非浸信會的[立場]。在荷蘭17世紀激進的浸禮會教派中,這種mijdinge(中間物)扮演著一個極重要的角色。
38 在17世紀初的阿姆斯特丹難民團體中,甚至在其內部的爭論與斗爭中這一點就已變得非常明顯。就如在蘭開夏郡對一個“執事”(ministrial)教會紀律的拒絕一樣,在教會中要求有一種平信徒準則和由平信徒執行的紀律,這一要求是因著克倫威爾時代的教會內部斗爭的態度而做出的。
39 長老的任命乃是在獨立派和浸禮會社群中長期討論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此與我們無涉。
40 1646年12月31日長期國會的條例被用來反對這個。它被視為對獨立派的一個打擊。另一方面,預言自由的原則也已為羅賓遜以書面形式所論證。Jeremy Taylor從主教制的立場出發對此作了讓步(The Liberty of Prophesying, 1647)。克倫威爾的“嘗試”這樣要求,只有在團體中得到六個合格的成員(中間要有四人為平信徒)的授權下,預言才是被許可的。在英國教會改革的早期,熱情的安立甘宗主教不僅經常容忍“練習”與“預言”,而且還對此加以鼓勵。在蘇格蘭,這些是教會活動的要素;在1571年它們又被引入了北安普頓。其它一些地方很快也跟隨之。但是伊麗莎白一直壓制它們,其結果就是她1573年反對Cartwright的聲明。
41 阿姆斯特丹的史密斯已經做出了這樣的訴求,在祈禱重生的時候,在他面前甚至不能有圣經。
42 在這些團體中,(Fox與相似領導一類型的)宗派主義者卡里斯瑪革命的開端往往是反對作官方控制的“薪俸階層”,為自由布道的使徒原則而戰,對于被圣靈所感動的講者來說是不需要報酬的。在Godwin這樣的會眾制的擁護者和Prynne這樣批評他的人之間,在國會中產生了激烈辯論,這一辯論反對他所宣稱的原則、他所曾經承認的“生存方式”;盡管如此,Godwin宣布只承認自愿提供的原則。只有對于執事的維持做出的自愿貢獻才應該被承認,這一原則在布朗派向詹姆士一世的請愿中得到了表達。(第71點:所以有對“教皇式生計”和“猶太教式宗教稅”的反對)
43 在1649年5月1號的人民協定(Agreement of the People)中,后者是對所有牧師都要求的。
44 故而循道宗的地方牧師就是如此。
45 在1793年循道宗廢除了授職和非授職的牧師之間的區分。由此,非授職的巡回牧師,當然還有布道團(他們是該派的重要特征),這兩者從此與圣公會所授職的牧師處于同等社會地位。但是與此同時,只有巡回牧師得到了巡回布道和圣事管理的壟斷權力。(圣事的自主管理主要通過他們來處理,但是與那些其成員準入資格裝得與以前一樣的官方教會的管理相比,也有段時間不同)在1768年以來,禁止牧師擔任普通的中產階級職位,于是一個新的“神職階層”產生了。
46 事實上,至少在英格蘭,大部分的“巡回團”都幾乎沒有什么教區,牧師的流動幾乎成了一個虛幻。不過雖然如此,到目前為止還堅持這一點,即同一個執事不能在同一個巡回團中服務超過三年。他們是職業牧師。不過,“本地牧師”(巡回牧師是從他們中間招募的)是一些有中產階級職位的人,并且擁有講道的執照,有一段時間這一執照原本只被授予一年。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因為禮拜與侍奉的位子太多了。但是首先,他們是“班”(組織)和靈魂治療的中堅。所以,他們乃是教會紀律[維持]的中心器官。
47 在其它問題上,克倫威爾對“圣徒國會”(Parliament of Saints’)的反對成為了大學的一個敏感問題。(在大學中所有什一稅都被徹底廢除,薪俸層[教牧]也消失了)盡管這樣,克倫威爾無法廢除這些文化機構,對于神學教育來說尤其如此。
48 在此根據1652年的規議,本質上也是根據1654年的教會憲章。
49 Gardiner給出了一個例子,見Fall of Monarchy, vol. I, p. 380。
50 威斯敏斯特懺悔(Westminster Confession)也(XXVI, I)建立了互相幫助的內外義務之原則。在所有教派中都有很多這樣的規則。
51 循道宗經常試圖以開除來懲罰那些訴諸世俗司法的人。另一方面,在某些例子中,他們也會建立某種權威機構,如果債務人不肯還錢,他們就會訴諸于此權威。
52 在早期的循道宗,沒有付薪的每一個案例都要被一個弟兄委員會所調查。因不能付報酬而導致債務是會招致開除的,這也是建立信用評級的方式。(Cf.見注解9中所引荷蘭宗教大會的決議)幫助處于危難之中的弟兄是被要求的,例如在Baptist Hanserd Knollys Confession(c. 28)中就保留如此特征,不過這并不至于對財產的神圣性產生偏見。偶爾地,也是非常嚴肅的(就如在1647年Cambridge platform中那樣,見edition of 1653, 7, no. VI)長老們被提醒他們的責任是反對那些“沒有天職”生活的成員,或是“惰于其天職”行為的成員。
53 循道宗就有這樣的表述。
54 在循道宗中,這些行為的認證最初每三個月就更新一次。舊的獨立派,就如前面指出的那樣,只給持證者授予圣餐。在浸禮會中,一個新加入社區者必須要有其原來的聚會團體的介紹信才能被接收。(cf. the appendix to the edition of the Hanserd Knollys Confession of 1689, West Chester, Pa., 1827)甚至16世紀初的阿姆斯特丹的三個浸禮會群體就已有了相同制度,從此以后它在每一地方都產生了。在馬薩諸塞州是1669年開始,資格證是從牧師和關心正統教義及行為的選民那里發出的,它可以證明持有者是有資格獲得政治公民身份的。這一資格證最初是用于行使圣餐準入功能的,后來也就代替了后者。
55 我們前面一再引用過道利(Doyle)的著作,他把新英格蘭地區與農業殖民地相對的工業化特征也歸因于此。
56 例如,道利談到了新英格蘭地區的地位狀況,那里構成貴族的不是“有產階級”,而是承擔著舊的宗教文本傳統的家庭。
57 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58 我們還要重點強調兩文(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首篇中的絕對定論。沒有將這一事實公布出來是我的評論家們的基本錯誤。在討論和埃及、腓尼基和巴比倫的倫理體系中的交易相關聯的古代希伯來倫理時,我們處在一個非常相似的位置上。
59 Cf.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66頁的其它評論中。在古猶太民族聚會團體的形成中,和古代基督教一樣,在相同的大方向上各自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猶太民族中,對親緣的社會重要性的拒絕是其條件,故而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中也有類似的影響)
60 Cf. The Livre des Métiers of the Pré? ?tienne de Boileau of 1268 (éd. Lespinasse & Bannardot in the Histoire Gégérale de Paris) pp. 211, sect. 8; 215, sect. 這方面可能還有許多其它的例子。
61 在此我們不能分析這種相當偶然涉及的關系,只能一筆帶過。
(引自中國藝術批評網)
(1)原文注解體例不統一,除尾注外還有部分腳注,筆者將其統一為尾注形式,部分次序也作了相應調整;(2)韋伯文中所提到的一些術語及專名,一般人殊難理解,筆者視乎必要在文中以[注-]的形式加以解釋。另外,香港浸會大學宗教系費樂仁(Lauren Pfister)教授在此文翻譯過程中提供了寶貴幫助,謹此致謝。
英譯本導言:韋伯的“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注1)
斯蒂芬·凱爾伯格(Stephen Kalberg)
本書中重印的“教派”一文(頁127-48)是寫于韋伯從美國返回德國后不久。以簡寫形式在1906年的兩份報紙發表(注2),他現在試圖讓更多德國聽眾接觸到他。通過1904年與美國近距離接觸[得到]的看法,韋伯希望對德國流行的種種陳詞濫調作一番影響。
“教派”一文更沒有《新教倫理》那么學術化。此文通過在美國中西部、南部、中大西洋各州及新英格蘭地區的旅行,反映了韋伯敏銳的社會觀察,不過其筆調沒有那么正式。盡管如此,他輕快的評論并不應被視為僅僅是要提供碎片式的“美國生活印象”。相反,韋伯通過對美國清教信仰在其起源250年后的命運,向他的讀者進行了追溯。
一方面,《新教倫理》提供了一個對具有特定宗教教義的信仰者的歷史調查,也通過對救贖的研究俯瞰了虔誠的內在心理動力與焦慮,還詳細描繪了支配美國、英格蘭、荷蘭和德國十七、十八世紀經濟行動之信仰和牧師實踐的影響。另一方面,“教派”一文則在二十世紀的開端考察了美國禁欲新教主義對社會群體的影響。韋伯涉及了團體成員資格之獲得與喪失的社會心理學,甚至還有它們與禁欲新教對工作與經濟行動的影響之相互關系。資本主義精神現在甚至比福蘭克林時代更加“入世”,韋伯希望簡短地歸納其主要影響。通過這種方式,“教派”一文補充了《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的探討,以及在有關信仰和行動之關系方面,天主教、路德教和清教之間的差異。因此,本書也將此文收入。
韋伯在“教派”一文中保持了一個穩定的視角,把問題集中于“[美國社會中]一度在所有禁欲主義教派中廣為流行的那些條件的直接派生物、剩余物和幸存物。”韋伯認為,“教派精神”具有多重遺產,它們構成了許多現象的社會學基礎,如社會信托、對世俗權威的懷疑態度、自治的實踐、還有美國人構筑公民團體的敏捷能力。
在此文中只談論了教派精神晚近的剩余物。韋伯強調,對于一個人加入某個社會團體的資格要檢驗其尊嚴、誠實和好的品質的觀念,新教教派是這一觀念最初的社會承擔者。作為“排他性”的組織,最初的教派只有在純粹的信仰基礎上才允許成員的加入。在作出決定之前,對于成員的道德品質要做嚴格考察。所以,一個人要是有正派的名聲的話,那自然就會擁有成員資格。教派能夠對其成員施加直接的社會影響,使他們不至于受誘惑偏離正道,正因為此,教派具有了證明其成員高尚行為的資格。
美國在1904年佩戴其標識所屬的世俗俱樂部或社團的徽章與領針,韋伯認為,這些東西和教派成員資格的作用相似,在建立在社會榮譽和個人德性方面吸引著人們。加入某個民間社團甚至就意味著人的社會地位的提升;這些人現在具有了可信賴的資格和“紳士”的角色。事實上,如果人們希望能在一個社區里被充分接納的話,這種成員資格是必不可少的。禁欲新教主義的影響在1904年作為“涉入”和“服務”社區的規范而明顯存在,由此,它在遙遠的國家和孤獨的個體“之間”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間團體。教派精神的這一成就構成了美國社會的一種基礎,使美國社會獨一無二地偏好創建許多這樣的團體。(注3)反過來,在其政治參與文化上和自治方面,這種能力構成其核心要素。
今天,大量的“規則”和各式俱樂部開始部分地承擔了宗教共同體的功能。幾乎所有對自己考慮的小商人都在其領子上佩戴某種徽章。不過,作為對個人“榮譽”的保證,這種形式的所有原型實際上都是教會共同體。(注4)
對于韋伯來說,“沒有人會懷疑清教主義在美國生活方式上的決定性作用。”
為了勾畫出美國社會圖景的這些特質,韋伯希望向德國普遍持有的那些陳腐之見挑戰,并在更廣的意義上,向德國人對于“現代社會”的共同觀感挑戰。在歐洲這樣一種信念廣為流行:資本主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將個人從“共同體”(Gemeinschaft)中割裂開來,使他們飄浮不定,并將其與“社會”(Gesellschaft)的其他人[的聯系]切斷。沒有了活生生的社會聯系,人們無目的地飄蕩,就像“原子”一樣互不聯系。對于涂爾干(Emile Durkheim)來說,這種情況導致了社會的反常和自殺率的提高。另外有些人談到了現代生活的“匿名”(anonymity)
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這樣看美國,他們認為這個國家實現了資本主義的最快速發展,正因為如此,美國社會一定是由一群缺乏個性、與他人缺乏非市場式聯系的個人組成的“沙堆”(Sandhaufen)。韋伯注意到美國中有組成社團的廣泛傾向,尤其重要的是這些東西源于(由其獨一無二的宗教傳統而來的)成員資格,因此韋伯希望向歐洲人的這種陳腐觀念徑直挑戰。此外,作為一個注重具體事實而非普遍“發展規律”的社會科學家,韋伯希望可以在資本主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共同經驗之外,另外找出,現代國家是如何作為系于宗教的特定歷史遺產之結果而變遷的。通過對不同具體事實的分析,韋伯認為,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有其自身的道路。對于他的德國同胞而言,韋伯希望告訴他們,盡管德國人對于自己國家的“原子化”社會抱有夢魘般的情結,但是這種現象的根源不是別的,它部分地就是源于德國的特定歷史與文化力量的聚合。
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上)(注5)
作者:馬克斯·韋伯
在美國,“政教分離”的原則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了。這種原則被執行得很嚴格,以至于沒有一個公認的官方宗教,對于國家來說,甚至要求公民接受某一種派別[的宗教]也被認為是違法的。對于宗教組織和國家政權間的關系之原則(注6),我們這里并不想討論其重要性。我們所感興趣的只是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僅僅在25年前,“無教派歸屬感者”的數量估計不過6%左右而已(注7);事實還在于,美國沒有像大多數歐洲國家那樣,為了賦予某一特權教會以歸屬感而給予它們高額的有效[國家]補貼,而且美國同時接受了大批的移民進入。
此外還應當看到,在美國教會的歸屬感與德國比起來,帶有更多地經濟上的負擔,尤其是對窮人而言。已公開的家庭預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埃瑞(Erie)湖的一座基本上完全由德國伐木工移民構成的城里,我個人聽到了許多關于在圣會中這種負擔的例子。以平均年收入1000美元計的話,他們出于宗教目的的定期奉獻幾乎為每年80美元。每個人都知道,在德國,甚至只要有這樣一筆數字的一小部分,都將會導致教會信眾大批流失。但是非常不同的是,在美國十五年到二十年前都從沒發生過這樣的事,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家最近越來越歐洲化以前,在所有沒有充斥歐洲移民的地方,這種緊密的教會意識都是隨處可見的。(注8)每一個以前的旅行者都指出,在美國正式的教會意識[的存在]是無可質疑的,和最近幾十年比起來,以前還要遠為強烈得多。我們在此對于這種情況的某一方面表示了特殊的興趣。
僅僅一代人前,當商人們自我組織起來并訂立新的社會契約時,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你屬于哪一個教會?”這個問題被一種并不魯莽且看來適當的方式問出,但是它肯定不會被隨意地問。在紐約的雙子城布魯克林,這一老傳統仍以相當大的程度被保持著,而且在那些越少受到移民影響的地方,這一情況就越突出。這一問題使人們想起了典型的蘇格蘭客餐(table d’h·te),四分之一世紀前,那兒的歐洲大陸人幾乎總是要面對這樣一種情況:一位女士問你,“你今天參加了什么侍奉?”或者,要是那些歐陸人作為最年長的客人而出現,且碰巧坐在最前方的凳子上的話,侍者在端著湯過來時將會請求他,“先生,請[領我們]祈禱。”在Portree(Skye)這個地方,在一個美麗的星期天我就碰到了這樣的問題,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說法,只有這樣說,“我是一個Badishe(注-德國南部地名)國教會(Landeskirche)的成員,在這里沒有看到我的教會的聚會。”那位小姐對這個回答很高興也很滿意,“哦,除了他本人的派別,他不參加任何侍奉。”
如果人們對于美國的這一情況觀察得更真切得話,他會很容易看到,在社會生活和商業生活中總是要牽扯到宗教歸屬的問題,這兩種生活是需要持久而信任的關系作為基礎的。但是我們前面也指出,美國政府并不介入這個問題。這是為什么?
首先,[自1904年來]一些個人觀察也許可以對此加以解釋。在一段臨近印第安區域的鐵路形成中,該作者坐在一位旅行的“殯葬所硬件”(即墓碑上的鐵字母)商人旁邊,偶然提及了依然非常強烈的教會意識。于是該商人這樣說,“先生,在我們這里,只要他喜歡,每一個人都可以信或不信;可是如果我要看到一個農夫或商人根本不屬于任何教會的話,我會連五十美分都不借給他的。如果他什么都不相信,那憑什么相信他會還錢給我?”這里的動機有一點兒模糊。
從一個德國出生的鼻喉專家的故事那里,問題會更為清楚一些,他在俄亥俄河邊的一座城市里開業,他向我說了他的第一位病人就診的事情。應醫生的要求,他躺在沙發上,接受鼻探測器的檢查。病人一站起來就莊嚴地作出強調,“先生,我是某某大街某某浸信會的成員。”醫生很困惑,這對鼻子的病和他的診斷有什么關系嗎,所以他謹慎地從一個美國同僚那里打聽。這位同僚微笑著告訴他,病人對自己教會的陳述僅僅意在告訴他:“不必擔心費用。”但是為什么要說得這么精確呢?或許這從第三個事件中可獲得更明白的理解。
在十月份一個美麗晴朗的星期天下午早些時候,我參加了一個浸信會的浸禮儀式。我同幾個親戚在一起,他們是來自幾英里外北卡羅林納州M縣偏僻地帶的工人。浸禮在一個池塘里舉行,池塘是由出自藍脊山脈(Blue Ridge Mountains)的一條小河注成的,老遠就可以看見。天氣很冷,夜晚還會結冰。大群的農民家庭都圍站在山坡之上;他們坐在自己的輕型兩輪小馬車中,有的來自鄰近,有的則來自大老遠。
穿著黑袍的布道者齊腰深地站在塘里。經過了不同的準備后,大約男女各十人穿著他們最好的衣服,一個接一個的進入了池塘中,他們見證了他們的信仰后就被完全浸入水中,婦女扶著牧者的手。他們起來之后,穿著濕衣服直哆嗦,然后步出池塘,每一個人都向他們發出“祝賀”。他們很快被裹上了厚厚的毯子,然后返回家中。我的一個親戚[對此]這樣評論,“信仰提供的無窮保護可以防止打噴嚏。另一個親戚站在我身邊的親戚,按照德國傳統來看是無教會的,他看著,鄙夷地向上唾了一口。他沖一個受浸者說,“喂,比爾,那水不冷嗎?”回答是異常熱情的,“杰夫,我心里有一些火熱的地方(地獄嗎!),所以我一點也不覺得冷。”在為一位年輕人受浸時,我的親戚大為吃驚。
“看吶,那家伙,”他嚷道,“我向你提過。”
浸禮結束后我問他時,他說,“為什么你希望那個人會受浸?他想在M縣開銀行。”
“在他周圍難道不是有許多浸信會徒可能做他的客戶嗎?”
“不全是這樣的,一旦受浸,他就會獲得整個地區的資助,他將會在競爭中壓倒每一個人的。”
在接下來關于“為什么”和“以什么手段”的問題中,產生了下面的結論:本地浸信會的接納只會導致接下來最謹慎的“審查”,然后會細致調查直到你的孩提時代的行為(瘋狂行為?經常上酒店?跳舞?看戲?打牌?過早出現債務?其他的荒淫行為?)。圣會仍然是嚴格堅持宗教傳統的。
圣會的接納被認為是一位紳士道德素質的絕對保證,尤其是那些商業活動中所要求的素質。浸信會把整個地區的存款都系于個人,并在沒有任何競爭的情況下給予他無限的信任。他是一個“被造的人”。進一步的觀察也證實了這些,至少情況是很相近的,在許多不同的地方都是如此。一般來說,只有那些屬于循道宗、浸信會或其它宗派,或者類似的非國教徒秘會的成員才會在商業上獲得成功。當一個宗派成員搬到另一個地方,或者他是一個流動商販時,他身上負有他所屬圣會的委任狀;這樣他會發現不僅與宗派[其他]成員能容易地接觸,而且首先,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尋得信任。如果他本人在經濟困難的時候沒有舞弊行為,那該宗派就會替他安排事務,向債權人[替他]作擔保,并在任何地方都幫助他,其根據一般都來自圣經的律令,mutuum date nihil inde sperantes [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路加福音6:35)
債權人的想法是這樣的,對方所屬的宗派為了自己的威望,不會讓債權人在代表該宗派的成員那里遭受損失;不過這一切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具有決定性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具有良好聲譽的宗派只可能會接受這樣的成員:他們的“行為”毫無疑問使他們獲得了道德聲譽的保證。
至關重要的是,宗派成員的身份就意味著一份道德素質的保證書,尤其是對個人的商業道德而言。與那些一個人“天生”就是其成員并被賦予超越義和不義之類榮耀的“教會”相比,這一點是截然不同的。事實上,一個教會就是一個組織榮耀、管理宗教恩典的公司,就好比一個捐款基金會那樣。僅僅從原則上而言,教會的歸屬感是義務性的,對于成員的素質它并不能證明什么。不過,一個宗派是一個自愿者組成的團體,它的成員原則上只包括那些宗教和道德上合乎規范的人。如果一個人發現他的成員資格在經過宗教上的審查之后,得到自動接受,那他就是自愿地加入了該宗派。在美國,這種選擇[的效果]經常被那些競爭性宗派導致的靈魂改宗而強烈地抵消――這部分的是強烈地受布道者的物質利益所影響,這當然也確是一個業已存在的事實。所以,在各個競爭性的教派之間,也經常存在著限制改宗的聯合協議。這種協議的形成可以看一些例子,如某個人已經離了婚,可是其婚姻從宗教觀點來看是無效的,為了防止這種人[鉆空子]輕易結婚,就會制定那樣的協議。那些較容易再婚的宗教組織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一些浸信會團體據說有時候在這方面比較松,而天主教和路德宗則以其嚴格規定而受到稱贊。不過據說這種立場也導致了這兩個教會的成員減少。
如果因為道德上的過錯而導致被所在宗派開除,這將意味著在經濟上喪失信譽,社會上喪失其地位。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1904)中,無數的觀察都表明,不僅教會意識本身正在快速消亡(盡管它仍然很重要);而且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非常重要的資質也可以確定是如此。在大都會地區,我在幾個隨便了解到的事件中都得知,那些對一塊未開發的地產打主意的投機商的常見做法如此:做出一副最謙卑的樣子,常規性的建立一座教堂;然后他從某一所神學院中雇用一個代理人,付給他五、六百美元,如果這個人能召集聚會,并使這個教堂滿堂的話,就把他安到像牧師這樣的顯赫位子上。我見到過明顯失敗并破落的教會。不過大部分情況下,牧師們據說都是成功的。諸如主日學校(Sunday School)之類的睦鄰聯系方式對于一個初來者而言,還是必不可少的,不過首先還是要與“道德上”可靠的鄰居相聯合。
在其它方面,不同教派之間的競爭也很激烈,如在聚會的晚點上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奉獻。在上流社會的教會中,音樂上的表現也和這種競爭有關。(如波士頓三一教會的一個男高音,他據說只在星期天唱,且收入8000元。)盡管有這樣激烈的競爭,各個教派之間的相互關系還是友好的。例如,在我所出席的一個循道宗的侍奉中,我前面提到的浸信會的浸禮儀式被當作一種壯觀而介紹給每一個人,以圖啟發他們。主要的是,這些圣會完全拒絕聽“教條”布道和自白式的特性。它們所唯一提供的是“倫理”。在那些我所聽到的面向中產階級的布道中,講道具有典型的布爾喬亞道德風格,毫無疑問是令人敬仰而又穩重的,同時又是以最溫和、最清醒的方式進行的。但是這些講道所傳達的是明顯的內在信念,布道者也經常被打動。
今天,[所屬]派別的種類是相當無關緊要的。一個人是共濟會成員,基督教科學主義者,基督再生論者還是貴格派成員,或者都不是,這些都是無所謂的。(注9) 決定性的因素在于,一個人在德性上經過一番檢查和倫理審查之后,經過“投票”被接納為一名成員,所依憑的是新教入世禁欲主義、因而也是古代清教傳統的道德要求。[現在]還可以看到相同的影響。
更詳細的調查還揭示出,存在著以“世俗化”為特征的穩固過程,源于宗教的所有現象都屈從于現代社會。不僅僅是宗教社團(當然也有宗派)對美國社會生活有這樣的影響。不過,教派的這一影響是逐步而緩慢衰退的。如果人們稍加注意,就會注意到醒目的事實(甚至十五年前就已出現了),在美國的中產階級(他們總是生活在十分現代化的大都會地區和移民中心之外)中間,有非常多的人在紐扣眼上裝了一個小徽章(五顏六色的),它讓人很容易就會想起法國榮譽軍團的玫瑰型飾物。當問這是什么時,人們一般會把它和某個帶有冒險和狂熱意味的名字相聯系起來。很明顯,它的重要性及其目的是這樣的:幾乎所有的團體在除了提供許多不同的侍奉外,還有安葬保險的功能。但是經常的,尤其是在那些最少受到現代裂變影響的地方,這些團體給成員提供了給予兄弟情誼般幫助的倫理教誨,這種幫助是每個成員都能做到的。如果他遭遇了并非自己造成的經濟困境,他可以做出這種吁求。這次我就注意到了一些這樣的例子,這一教誨所遵循的原理就是:“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或者至少其中很少利益因素。很明顯,這樣的教誨是具有兄弟之誼的成員們所愿意認可的。此外,一個主要的問題是,成員資格的重新獲得要通過對道德價值的調查和肯定,并經由投票表決。所以在紐扣洞上的徽章就意味著,“我是一個經過了調查和審查而得到紳士身份的人,我的[教派]成員資格保證了這一點。”而在商業生活中還首先意味著:通過了信譽保證的檢驗。人們可以看到,商機經常受到這些正當性的決定性影響。
所有這些現象都基本上限定在中產階級層面,不過它們似乎正在處于快速裂解之中,至少對于宗教組織是如此。一些有教養的美國人常常簡單地忽略了這些事實,或帶著一些憤怒鄙之為“騙局”或倒退,或者壓根就否定這些事實;許多人實際上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威廉詹姆士向我確證了這些事情。不過這些[傳統]的幸存者在許多不同的地方仍然存在,有時候其形式顯得有些怪異。
這些團體是典型的通往上層社會的交通工具,它們由企業界的中產階級人士圈子人士組成。它們所起的作用是,在中產階級的廣泛階層(也包括農場主)中,散布并維持布爾喬亞式的資本主義商業倫理。
眾所周知,在美國的億萬富翁和信貸大亨的“帶頭人”(promoters)、“工業領袖”中有不少人(最好說是老一代人中的大多數),他們在形式上是屬于這些教派的,尤其是浸信會。不過,本質上而言,這些人經常是由于純粹的傳統因素而聚到一起的,和在德國一樣,這樣做是為了使自己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獲得正當性,而不是使自己作為商人而取得正當性;在清教時代,諸如此類的“經濟超人”并不需要這樣的支撐,他們的“宗教虔誠”當然也時常是非常模棱兩可的。首先是正在形成的中產階級、或從其中往上走的階層,成為了那些特定的宗教導向的承擔者,人們實際上可以把他們中的一些人看作是僅僅由偶然因素決定的。(注10)
不過我們一定不能忽視,如果沒有一種生活方式的原則和這些資質的普遍存在,如果不是這些資質通過宗教團體而得以維持的話,即便在美國,今天的資本主義也是不可能像它本來的樣子的。在任何經濟領域的歷史中,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夠塑造出像摩根(Pierpont Morgen)、洛克菲勒、古爾德(Jay Gould)等那樣的資本主義形象來,[這不同于]封建主義和家父長主義時代的僵化。他們所用以掌握財富的唯一的技術手段已經改變了(當然如此!)。他們屹立著,站在“善與惡的彼岸”。但是,不管人們對他們在經濟轉變中的重要性估計得有多高,也不能無限夸大,在主導一個特定時代和特定地區的經濟氣質中,他們永遠也不是決定性的。首先,他們不是特定的西方中產階級氣質的創造者,也不會變成它的承擔者。這里不從細節上討論這些美國宗教派別和許多團體及俱樂部(它們是幾乎獨一無二的)之政治與社會重要性,他們的成員的入會都是經由票選的。在一系列諸如此類的獨一無二團體中,最后一代典型的美國佬的完整生活引導著它們,從學校的男孩會(Boys’ Club 注-指表現男子勇氣的社團)開始,到運動員會或希臘字社團(Greek Letter Society注-指用希臘文來標志自己名稱的社團),或某些方面的另一類型學生俱樂部,接著是許多著名的商業與中產階級俱樂部,最后是大都會的財閥俱樂部。獲得[它們的]承認就等于獲得了向上爬的門票,尤其與在一個人的自我情緒廣場前樹立的許可證差不多。獲得它們的承認也意味著對自我的一種“證明”。一個在校的大學生如果沒有被任何會社(或準社團)所接納,不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如同某種賤民(我注意到有因為未獲接納而自殺的情況)。一個如是的商人、職員、技術員或醫生通常就獲得了毫無疑問的服務能力。今天,無數這類的俱樂部成為了通向貴族地位團體趨向的承擔者,這類團體是當代美國社會發展的特征。這些很有名的地位團體在側面發展,它們與赤裸裸的財閥統治形成了鮮明對照。
在美國,純粹的“金錢”本身也能買到權力,但是卻買不到社會榮譽。當然,它也是掌獲社會尊嚴的一種手段。在德國和任何其它地方都是如此。除了德國之外,[其它地方]社會榮譽的適當途徑來自于對封建地產的購買與繼承,及有名無實的貴族身份的獲得,這些也反過來加速了貴族“社會”第三代的認受性。在美國,老傳統尊敬白手起家的人而不是繼承者,通往社會榮譽的階梯由在某所院校的友誼認同度所構成,從前則是一個特定的教派(例如,在紐約的長老會教會中,人們可以發現軟沙發和扇子)。現在,屬于某一個特定的俱樂部比什么都要重要。此外,這樣的家庭很重要(它們位于那些在中等規模城市里幾乎從來不缺少的“街道”上),那些諸如此類的服裝和運動也是如此。只是在最近,來自朝圣教父,Pocahontas(注-印第安女性名字)與其它印第安婦女等等之類的關系也變得重要了。這里并不欲在細節上討論他們。出現了許多關注重建財閥的家系諸如此類的代理及翻譯機構。所有這些現象――經常非常稀奇古怪,屬于一個歐洲化了的美國“社會”的廣闊領域。
從過去直到現在,具體的美國式民主的一個確切特征就在于,它的結構不同于由許多個人所構成的無定形的沙堆,而是由非常排他但卻又是自愿組成的團體所構成的復雜結構。直到不算太久前,在職務和教育方面,這些團體仍然不認可生來及繼承來的財富之尊嚴,也不承認官方職務與教育文憑的尊嚴;至少在世界上其它地方,他們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還是非常少見的。不過即便如此,這些團體也遠不是對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張開雙臂。可以確信的是,十五年前,一個美國農場主如果不在正式介紹后讓他的客人與工人“握手”的話,他就不會領著客人從他正在犁田的雇農(天然的美國人!)旁經過。
以前,在一個典型的美國俱樂部里,沒有人會記得有這樣的事,如兩個成員會以老板和職員關系一起玩臺球。這里絕對隨處可見的是紳士的平等性。這樣的事在日耳曼-美國俱樂部里也不是經常有。我問過一個在紐約的德國商人(他有著最好的漢薩式的姓名),為什么所有人都試圖獲得一個美國俱樂部的接納,而不是一個設備非常良好的德國俱樂部時,他的回答是,他們(日耳曼-美國人)的老板偶然會和他們一起打臺球,可是僅僅讓他們覺得老板們自我感覺這樣作很“仁慈”。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工人的妻子和工會成員一起吃午飯,她們在著裝和行為上可以隨心所欲,在中產階級女士們看來是有幾許老土和糟糕的式樣。
他希望自己在這一民主內能夠被充分接納,不論自己處在何種地位,他不僅要必須遵循資產階級社會的傳統慣例(包括了對男人著裝的嚴格要求),而且作為一種規矩,他必須能夠顯示出自己成功贏得了某個組織的票選接納,而不論該組織是教派、俱樂部還是友誼會團,這樣他才能為自己獲得充分的[身份]正當性。要在這樣的社團里呆下去,他也必須得證明自己是一個紳士。而在德國的類似組織中,組成的關鍵在于庫魯爾(Couluer)(注11)的重要性、及商業和貿易領域的預備官員委員會、還有通過決斗而獲滿足從而得到高位資格的重要性。它們的性質都是相同的,不過其導向及物質后果就顯著的不同。
如果他沒有被成功接納的話,那就不能算是一位紳士;如果他像在一般的德國人中間那樣(注12),對此表示輕視,那他將會不得不走上一條坎坷之途,尤其是在商業上更是如此。
但是盡管如此,我們這里并不想分析這些條件的社會意義,這一點前面也說過了,它們牽涉到深刻的轉型問題。首先,我們感興趣的事實是,需要經由票選入會的世俗俱樂部和社團的現代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世俗化過程的產品。它們的地位源自這些自愿社團的原型,即教派的非常獨一無二的重要性。實際上,它們根植于那些最初的美國佬樂園之家――北大西洋諸州的教派。讓我們先回顧一下,美國民主中的普選(只限于白人!黑人與所有有色人種甚至今天在事實上仍無普選權),還有類似的“政教分離”,這些都只是最近才達到的成就,它們基本上發端于十九世紀。讓我們記住,在殖民地時代的新英格蘭中心區域,尤其在馬薩諸塞,州的完全公民資格的獲得的先決條件(此外也有些其它先決條件)是,獲得教會的完全成員地位。宗教圣會事實上決定著政治公民身份的被接納與否。(注13
這一決定所根據的是,某個人能否在最廣義上通過行為證明自己的宗教資格,就像在所有清教宗派中例子那樣。直到獨立戰爭前不久,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派才在較輕的意義上可以算是該州的主人。這已成為了的確的事實,不過從形式上說,他們還不是具有充分的政治公民身份者。只是依靠了大范圍的重新劃分選區,他們才成為政治上的主人。在教派圣會的充分參與權上,尤其在領取圣餐的權利上能夠被接納,這具有極重要的社會意義,由教派發展出的禁欲主義職業倫理在其最初階段,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而現在在教派中的社會意義是由這一倫理所哺育出來的。可以證明的是,在包括歐洲在內的任何一個地方,就如在上面所說的美國的個人經驗表明的那樣,禁欲主義教派的宗教虔敬幾個世紀中都是如此發揮影響的。
當關注這些新教教派的宗教背景時(注14),我們在書面檔案中發現這樣的事實(尤其是在整個十七世紀的貴格派和浸信會中),有罪的“世界之子”彼此在商業上不信任,但是他們在虔誠的宗教之義中產生信任,他們為此而一再發出歡呼。(注15)
所以,他們僅僅通過虔誠而委托并儲蓄他們的錢,他們也在這一范圍的店鋪中交易,因為在那兒、也只有在那兒,他們才有誠實和可靠的價格。如所知的,浸信會總是針對一個原則首先宣布提出這個價格策略。此外,貴格派也作了這一宣布,下面引用了一項材料,愛德華·伯恩施坦在當時提醒我們注意:
但是事實上,價格政策不僅僅和土地方面的法律有關,這些土地是那些堅守他們的諾言和神圣約定的最初成員所擁有的。在他們的商業利益中,這一特性對于他們來說都是實實在在的。在他們以社團的方式首先出現時,他們以作商人為苦差事,因為其他人由于不喜歡他們[宗教]儀式的特性,不愿意做他們店里的顧客。可是在短時間內,當他們把農村的商業也轉入手中時,外人大聲疾呼排斥他們。這一呼吁部分地源于在他們和其他人的所有商業協定都有嚴格的免稅權,也因為他們從不為他們所賣的商品去搞雙重價格。(注16)
對于那些通過奉獻和行為讓神悅納的人,神會保佑他們致富,這樣的觀點事實上在全世界都有。不過,新教教派有意識地將這一觀念和這種宗教行為聯系起來了,這從早期資本主義的這一原則可以看出:“誠實是最好的策略”,這一聯系不是僅在這些新教教派中有,但是只有在他們中間,這一特征才具有持續性和穩固性。
完整的典型資產階級倫理的來源范圍從普通人直到禁欲主義宗派和非國教徒的密會,它也是直到目前為止為美國的教派所實踐的倫理。例如循道宗有這樣的禁令:
(1) 禁止在買賣中討價還價;
(2) 禁止在關稅付清之前進行商品交易;
(3) 利息的收費率不得高于國家法律的規定;
(4) 禁止“聚斂土地財富”(指的是把投資資本轉化為“固定財富”);
(5) 在不能確保還債能力的情況下禁止借債;
(6) 禁止各種奢侈行為。
但是這里所討論的不僅僅是在細節上已經討論過的倫理問題(注17),那樣的話要返回禁欲主義宗派的早期開端。而首先在于,社會獎懲、紀律手段以及――一般的說來――新教教派的各個分支的整個組織基礎都要追溯到這些開端。它們在當代美國的繼承者乃是生活的宗教規則之派生物,這些派生物的社會功能的效率都是極高的。讓我們在此簡短地澄清這些教派的本質,還有它們的模式與功能之指向。
在新教當中,“信仰者的教會”這一原則首先明顯來于1523-24年間蘇黎世的洗禮派。(注18)這一原則將聚會只限于“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它意味著,這是由從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得到真正認可的人所組成的一個自愿團體。托馬斯·閔采爾否定嬰兒受洗;但是他沒有采取下一步驟,也即要求成人像嬰兒受洗一樣重新受洗(再洗禮主義)。蘇黎世的洗禮派追隨閔采爾,于1525年引入了成人洗禮(可能也包括再洗禮主義)。流動的旅行者和工匠是洗禮派運動的主要承擔者。在每一次受到鎮壓后,他們都將它帶到一個新的地方。這里我們不打算再細節上討論這些舊的洗禮派、門諾派、洗禮派和貴格派的自愿入世禁欲主義的個人形式,也不打算重新描述,每一種禁欲派別是如何一再落入同樣的路向的,包括加爾文派(注19)和循道會。
這種情況出現在要么是教會內部模范性的基督徒非國教徒密會中(虔敬派),要么是其他宗教上的“充分公民”(具有無謬誤的正當性)之群體中,他們是掌握著教會的主人。其他的成員僅僅屬于消極身份團體、或服從紀律的少數派基督徒(獨立派)。
在新教中,作為榮耀管理義務性組織的“教會”和作為宗教上合格者的自愿團體之“教派”,這兩種[不同的]結構原則在內外兩方面都有沖突,從茨溫利到Kuyper和St·cker,這一沖突幾個世紀來一直存在。我們在此僅僅希望考慮那些自愿主義原則的后果,這些原則在對其行為的影響上具有實踐上的重要性。此外,我們僅僅回顧這一事實,是圣餐純潔的決定性觀念,及因此對不合格者的排除,在那些沒有形成教派的派別中,也會產生一種處理教會事務的方式。尤其是預定論的清教徒,正是他們有效地由此達成了教派的紀律。(注20)
對基督教團體而言,圣餐的關鍵社會重要性在此是很明白的。對教派本身而言,神圣宗教團體純潔性的觀念在其最初時期,還是深具決定性的。(注21)很快的,第一個穩定的自愿主義者,布朗恩(Browne)在其“迫切宗教改革論(Treatise of Reformation without tarying for anie)”(可能是1852年)中強調,之所以在圣餐上要對“邪惡之人”維持宗教團體之壓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對主教制度和長老制度的拒絕。(注22)長老會徒勞無益地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在伊麗莎白時代(Wandworth會議),這已經成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注23)
有關誰應決定從圣餐中被排除者,這在英國革命期間的國會中是一個不斷出現的重要問題。一開始(1645)由執事(ministers)和長老,即平信徒自由決定這一議題。國會試圖處置這些事關開除的議案;所有其它的議案都是依靠議會而做出的。這被稱為“國家全能主義”(Erastianism),威斯敏斯特會議(Westminster Assembly)對此表達了尖銳抗議。
獨立派黨人取得優勢,因為除了得到認可的本地居民外,它只接納屬于宗教團體的人。只有得到合格的成員的介紹,外來聚會團體的成員才會被接納。資格證明書(介紹信)也在十七世紀出現了,它是在從一地往另一地或旅行時被授予的。(注24)在官方教會內部,巴克斯特的非國教徒密會(協會)于1657年被引入十六個縣,它們被設立成一種自愿性的審查機構。這可以讓執事更容易鑒別合資格者,并把那些名聲不好的人從圣餐中排除。(注25)威斯敏斯特會議中的“五抗議兄弟會”(five dissenting brethren)――這是居住在荷蘭的上層階級的避難所――也是如此,他們提出允許在教區旁邊存在由自愿者組成的圣會,并賦予他們票選宗教大會代表的權利。新英格蘭的全部教會史都充滿了圍繞這類事情的沖突:誰能被圣禮所接納(為一個主教,這是一個例子);未被接納者的孩子能否受洗(注26);還有在什么情況下后者可以被接納,及諸如此類的問題。困難在于,那些高貴的人不僅要被允許接受圣餐,而且還不得不接受它。(注27)所以,如果信仰者自己懷疑自身的價值,并遠離圣餐的話,這一決定本身不會消除他的罪。(注28)另一方面,為了能保持純潔,要讓那些無資格者、尤其是應受指責者(注29)遠離宗教聚會,圣會也是負有聯合責任的。所以通過一個負有榮耀的高尚執事,聚會團體對于圣事的管理是負有聯合且特別的責任的。這樣,教會章程最初的問題又重新出現了。巴克斯特做了折中的提議,在緊急情況下,來自不合格執事(即其行為是有問題的)的圣事應當被接受,但他試圖調和的做法并無成效。(注30)
[在這個問題上]在早期基督教時代,古代的多納圖派持個人卡里斯馬的原則,它和那種把教會視為管理恩典的機構的原則(注31)是截然對立的。通過教牧者的character indelebilis(不可損毀的完整性),在大公教會中激進地建立起了恩典制度化的原則,在宗教改革后的官方教會也是如此。獨立派的立場是激烈且不容妥協的,它們是建基于把圣會當作一個整體的宗教責任上。除了兄弟情誼,執事的德行也成為宗教聚會所考慮的。在此顯示了這些事情是怎樣通過其原則而成立的。眾所周知,荷蘭的Kuyper分裂派在最近幾十年里曾有深遠的政治影響。它源于下面的形式:為了抗議荷蘭國教會(Herfomde Kerd)的大宗教會政府(Synodal church government)的宣言,一家阿姆斯特丹教會的一幫長老,當然是平信徒,以首席執事Kuyper(他也是一普通的平信徒長老)為首,拒絕給聚會之外的布道者給予資格證書,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這些外部的布道者是不合格者或不信者。(注32)就實質上說,十六世紀的長老會與獨立派確實是互有敵意的;最重要的后果是由圣會的聯合責任所肇端的。與自愿原則幾乎一致的是,合格者是被聚會團體所自由接納的,當然僅限于合資格者,我們發現地方圣事團體的支配原則就是如此。通過對個人的調查和熟知,只有本地宗教共同體可以裁決一個成員是否合格。但是跨地方團體的教會政府就不能如此,不管此政府的管理在選舉上有多么自由。要是成員的數量被限制的話,地方圣會可以進行挑選。所以原則上來說,這只適合于相當小規模的圣會。(注33)
要是團體太大了,要么就像虔敬派那樣形成秘密集會,要么反過來,這些成員像循道宗那樣被組織起來,成為教會紀律的承擔者。(注34)這些自治圣會所具有的超常嚴格紀律(注35)構成了第三條原則。這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這和圣事團體的純潔性旨趣有關(如貴格派中,和祈禱者團體之純潔性旨趣有關)。實際上,禁欲主義宗派的紀律比任何教會的紀律都要嚴厲得多。在這方面,教派可與僧侶序階相比。教派紀律也和僧侶的紀律很相似,因為它建立了見習原則。(注36)與那些官方新教教會不同的是,由于道德犯規而被開除的人通常被拒絕與其他成員交談。故而教派對他們是實行絕對排斥的,包括在商業生活中。有時候,除非萬不得已,教派是避免與并非自己兄弟的人發生聯系的。(注37)而且教派將這種超級的紀律權置于了平信徒之手。在上帝面前,沒有什么精神權威可以承擔團體的聯合責任。甚至在長老會中,平信徒長者的分量也是很重的。不過,獨立派、甚至還有浸信會則不懈地與神學家的權威或統治作斗爭。(注38)正是由此,這一斗爭自然導致了平信徒成員的職事化,他們通過自我管理、警告、甚至可能開除來發揮道德控制的功能。(注39)教會平信徒的統治也部分地表現在他們對自己布道之自由(預言的自由)的尋求上。(注40)為了讓這一訴求合法化,向早期教會團體的情況作了參考。這一訴求不僅對于路德派的教牧官職(pastoral office)觀念是離經叛道的,對于長老派的神命(God’s order)觀念也是如此。平信徒的統治還部分地表現為,他們反對任何職業神學家和牧師。唯一應得到認可的只有卡里斯馬,而不是訓練和官職。(注41)
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下)
貴格派則堅持這樣的原則,在宗教聚會中任何人都可以發言,不過他只能談他被圣靈的感動。所以那里根本沒有職業執事。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可以確信的是,直到今天,沒有任何地方因此產生過大不了的后果。正式版的“傳奇”是這樣說的,那些在聚會侍奉時被圣靈所特別蒙納的成員在聚會的時候,坐在一圣會對面的特別長凳上。在深深的靜默中,等待圣靈的人們掌控著他們中的一個(或聚會的某些其他成員)。但是在一家賓夕法尼亞學院的侍奉中,與我的愿望不幸的相反的是,圣靈沒有控制那位坐在凳子上的樸素而美麗的女士――她的卡里斯馬受到高度贊揚。相反,大家一致同意圣靈控制了一位勇敢的學院圖書管理員,他就“圣徒”這個概念作了一通很博學的演講。
可以肯定的是,其它教派并沒有得出這樣激進的結論,至少沒有想要一勞永逸地如此。不過雖然如此,執事要不是作為“雇員”而積極活動的話(注42),也會為了自愿的光榮捐獻而侍奉。(注43)其侍奉可能還是一種次級的職務,并僅僅是從事其費用的重新募集(注44);[不然的話]要么他被解職;要么就是作為一種巡回布道(注45)的傳教組織,僅僅偶爾沿著相同的路線工作,如在循道宗就是如此。(注46)只要(傳統意義上的)官職和相關的神學資格得到維持(注47),這種技術就會被視為是一種純粹技術性和專門性的特權。不過,真正決定性的要素是榮耀狀態下的卡里斯馬,而其權力機構就通過調整自己來辨別它們。
權力機構,如克倫威爾時代的triers(控制宗教資格許可證的地方實體)和ejectors(執事紀律之官職)(注48),必須要檢查執事侍奉的適當性。權力機構的卡里斯馬性格被認為是以這樣的特征保持著――它與團體自身成員的卡里斯馬特征的保持方式相同;如克倫威爾的圣徒軍只允許宗教上合格的人進入他們的圣餐,所以如果一個軍官出自不符他們宗教資格圣事之團體的話,克倫威爾的士兵就會拒絕作戰。(注49)
在教派成員中,早期基督教兄弟之情的精神仍內在地隨處可見,至少在早期浸信會和其衍生派別中是如此;至少也會對此做出要求。(注50)在某些宗派中,打官司被當作一種禁忌。(注51)除非萬不得已,相互幫助是一種義務。(注52)自然,與非成員間的商業交易不會遭到干涉(除在極端派別團體中會偶爾為之)。
不過從他們的自我理解來看,他們是更偏好于兄弟之情的。(注53)從一開始,人們看到許可證制度就是如此(與成員資格及其行為有關)(注54),它在其成員遷移到另一地方的時候被授予。貴格派的慈善事業高度發展,由于其所承擔的這些負擔的緣故,他們[對此]宣傳的勁頭也就減弱了。圣會的凝聚力很強,所以它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是新英格蘭定居者之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與南方不同的是,新英格蘭的居民點普遍密集,并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的城市化特征。(注55)
很明顯,在所有這些方面,美國教派和類似教派的組織的現代功能被揭示出來了,就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那樣,它們是曾經在所有禁欲主義宗派和秘密集會中廣為流行的,而其現代功就是那些情況的直接派生物、剩余物和積淀物。今天它們也正在走向衰敗。從一開始,這些教派主義者就明顯有一種非常排他性的“孤芳自賞”(pride in caste)。(注56)
現在我們來看,在這整個發展過程中,是哪一部分對我們的問題過去和現在具有實際的決定性作用呢?在中世紀,被逐出教會也會有政治和民事上的后果。而且就形式上而言,在自由度上比教派要更為苛刻。此外,在中世紀只有基督徒才是充分的公民。在中世紀,也有可能通過教會的紀律權力來反對一個不還債的主教,舒爾特(Aloys Schulte)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這一原因使得主教比世俗諸侯具有更高的信用度。與此相似,一個普魯士副官如果不能清償債務,那就會被解職,正是這一事實也使得他能夠擁有較高信用度。德國學生的友情也與此相同。在中世紀,教會所擁有的口頭悔改和紀律上權力也是如此,它可使教會紀律有效發揮作用。最后,通過訴諸法律,[債務上的]誓言也可以保證把債務人革出教門。
盡管如此,在所有這些例子中,與那些新教禁欲主義所哺育或壓逼出來的行為模式相比,經由這些條件和手段所得到贊同或反對的行為模式與前者還是總體上不同的。我們可以以副官、或友誼會的學生、也可能是主教作為例子,信用度的提高肯定并不依靠與商業行為相應的個人資質的培養;直接看看下面的評論:即便這三個例子的影響是相同的,它們也是一非常不同的方式發生作用。首先,像路德宗那樣的中世紀教會紀律是處于執事官員的掌控下起作用的;第二,通過這些威權式的手段,這一紀律才得以最有效的發揮作用;第三,它只是對具體的個人行為實施獎懲的。首先,至少部分的及經常是全部的,清教徒與教派的教會紀律是授予平信徒之手的。第二,它要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第三,它培養或選擇了不同的品德,如果人們希望如此的話。最后一點是最重要的。
為了能夠進入團體的圈子里,教派(或非國教徒密會)的成員必須有某種品德。這些品德對于理性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重要的,這在第一篇文章里也指出了。(注57)為了能呆在這個圈子里,成員必須要一再證明,他賦有這些品德。他持續不斷地培養這些品德。因為就像上天對他的賜福,他所處的全部社會地位現在都要依靠他對自己信仰的“證明”。在減輕一個人的罪的手段上,天主教的懺悔是反復地來自內心的巨大壓力,而教派成員則面對這種壓力而不斷地加以控制。關于中世紀的正統和異端宗教團體是如何成為新教禁欲主義派別的先驅的,這些在此就不想討論了。
根據各種情況來看,通過保持其在團體的圈子里地位而來培養自身資質的做法是最有力的了。所以,教派的穩定而至高無上的倫理紀律是和權威主義的教會紀律相聯系的,而理性化的培養與選擇[方式]是和秩序與禁忌相聯系的。
幾乎所有的其它情況也表明,清教教派是禁欲主義的內向形式的最不同尋常的承擔者。此外,他們是最穩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唯一穩固的普世大公教會的反對者,他們是恩典管理的義務性組織。在這些資質的培養上,清教教派把關于社會地位的個人利益置于了強有力的地位上。所以,從各個方面說,個人的動機與自身利益也在產生和維持“中產階級”上發揮著作用。清教倫理[體現在]所有它的分支中。究其深遠的及無與倫比影響力而言,這絕對是決定性的。
需要一再指出,不是宗教的倫理教義,而是它的倫理行為方式在發揮著獎懲作用。(注58)這種獎懲是通過救贖的個別之善的條件和形式而發揮作用的。并且在社會學意義上,這樣的行為構成了一個人的具體“倫理”。某種程度上,對清教而言,那種行為是一種生活的系統化和理性化的路向,它為現代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在救贖意義上,這些獎懲是在上帝面前來證明自己的(在所有清教派別中都可以發現這一特征),而就清教教派內的社會地位而言,它是在控制著自己的人面前來“證明”自己的。這兩個方面互為補充,又在同一方向上運作:它們有助于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傳播。它的具體精神氣質是:現代布爾喬亞中產階級的精神氣質。就現代“個人主義”而言,禁欲主義宗派和秘密集會構成了其最重要的歷史基礎之一。它們激進地突破了父權制和權威主義的限度(注59),此外它們還強調了順服上帝而不是人,這些尤其重要。
最后,為了理解這些倫理影響的本質,需要作出一個比較性的評論。在中世紀的行會中,一直有對其成員的一般倫理標準的控制,它與禁欲主義清教教派紀律的運作方式相似。(注60)但是行會和教派對于個人經濟行為的影響就必然不同,這一點是很明顯的。行會把同職業者聯合在一起;這樣它聯合了不同的競爭者。它這樣做的目的在于,限制競爭,并理性地尋求通過競爭而得到的利潤。行會培訓出了“民事”素質,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中產階級“理性主義”的承擔者(對此不想予細節上討論)。行會是通過“永久的政策”及傳統主義而完成這一點的。
另一方面,通過將倫理上合資格的信仰追隨者加以培養和選擇的做法,教派將人整合起來了。他們的成員資格并不是基于學徒資格,也不是基于和職業技術有關的家庭關系。僅僅是在形式正義和條理化的禁欲主義上,教派控制和指導著其成員的行為。它與物質性永久目標無關,后者被認為是有礙于對利潤的理性尋求的發展的。行會成員的資本主義成功逐漸損害了行會的精神(在英法都是如此),所以資本主義的成功也[反過來]受到了阻礙。但是只要法律許可,教會兄弟的資本主義成功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和榮耀,并且也提高了教派的威望和宣傳機會。所以這樣的成功是受歡迎的,這在前面業已指出了。行會的自由勞動力組織在其西方中世紀的形式中,當然不僅是一種阻礙(這和他們的本意也相違),而且也是勞動力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先決條件,這一點或許也是必不可少的。(注61)但是當然,行會不能促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只有禁欲主義宗派的條理化生活方式才能賦予它合法性,并且也給現代資本主義氣質的經濟“個人主義”沖動蒙上一層光環。“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Hans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in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s of Capitalism, intro & trans by Stephen Kalber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p. 127-47.
【注釋】:
1 這篇文章有個唯一的譯本,就是本書中的,譯者為Hans H. Gerth和C. Wright Mills。為了與《新教倫理》一書在術語上統一,少數用語作了修改。書目方面的信息見此文p. 263的第一個腳注。
2 現在有早期文章的兩個譯本,這里所提供的版本是韋伯在1920年擴展的。此外還加了大量的注腳。
3 當然,更早還有托克威爾強調美國社會的這一發達的能力。不過,就組建團體的傾向(這一點與美國有“多數人暴政”的傾向是相對立的)而言,他的解釋在許多方面與韋伯有所不同;托克威爾強調平等主義、商業利益以及個人利益,而韋伯則指向禁欲主義新教的宗教遺產。
4 就某個人的社會地位而言,韋伯極端強調進入一個社區的教會和俱樂部的重要性(例如Rotary, Lion等),這會導致把美國描述為一種“好的封建主義”的社會。
5 在《法蘭克福時報》(Eastern 1906)出了一篇文章新的、擴充了的綱要,后來又在《基督教世界》(1906,pp. 558ff., 557ff.)作了一些擴充,題目為“教會與教派”。我一再將此文作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補充。現在又將它重寫,其原因在于,教派這個概念是由特洛爾奇在他的《基督教會的社會學說》中加以徹底闡釋和運用的,我自己也使用了它(將它與“教會”的觀念相對),并且也很喜歡這個概念。所以,概念上的討論盡管在《新教倫理》(pp. 221, note 200)中已指出了其必要性,但在此還是輕易省略了。這篇文章只收入了那篇文章顯而易見的補充材料。
6 考慮到天主教徒選票的重要性,還有對告解學校(confessional school)的資助;這一原則常常只是理論上的。
7 在此對其在細節上并無興趣。可以參看“美國教會史系列”的各卷,這一著作質量參差不齊。
8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僅美國最高法院開庭的時候,就是每一個黨派的傳統中,都有這種公開的祈禱,它們構成了一套煩人的儀式。
9 在一所東部大學中教閃米特語的助教告訴我,他很遺憾沒有成為“講席擁有者”(master of the chair),所以他打算重返商界。當問這樣做有什么好處時,回答是:作一個流動商人或貨主,他能夠充分表現自己,使自己得到令人尊敬的名聲。他能夠擊敗任何競爭者,并使自己的價值得到最好的體現。
10 在美國,這些方面所表現出的“偽善”和傳統的投機主義并不比德國更強,畢竟,在德國,一個“沒有宗教歸屬或取向的”官員或公仆也是不可能的。有一位柏林的(雅利安人!)市長大人沒有得到官方確認,就是因為他沒有讓自己的一個孩子受洗。這些傳統的“偽善”有不同的表現:德國的官員職位,美國的商業機會。
11 學生友誼,與“希臘字社團”相對。
12 不過前面也提到過了。失去德國國籍很關鍵的一點在于,(在學校或之后)進入一個美國俱樂部。
13 在往新英格蘭移民期間,這些宗教聚會組織經常是先于政治社會而存在的。(其以Pilgrim Fathers[注-指最早到美國的宗教逃亡者與教士]協議的形式而廣為人知)故而,1619年多爾切斯特(Dorchester)移民首先這樣做了,他們在移民之前組織了一個教會,由此把自己組織起來了,他們選出了牧師和教師。在馬薩諸塞殖民地,教會在形式上被認可為徹底自治的團體,不過另一方面,只有屬于其者和具有成員資格者才能成為公民。與此相同,在紐黑文教會(在它在康涅狄格州被組織起來之前,鄉鎮是有義務維持教會的)一開始也如此,教會成員資格和善行(意味著可領圣餐)也是成為公民的先決條件。(這也是獨立派以嚴格的紀律來表達對長老派的不滿)這就立即意味著更為寬松的實踐,因為在紐黑文的教會被整合起來之后,這種資格的限定是比較寬泛的,它包括那些宗教上不那么令人討厭的個人。甚至在17世紀,在緬因和新罕布什爾州的整合上,馬薩諸塞不得不放寬了對[享有]政治權利之宗教資格的嚴厲限制。在教會成員資格的問題上,也不得不作出了這樣的承諾,最有名者就是1657年的Half-way Covenant(注-指某些教友不屬于教會但是也能參與教會事務)。此外,凡是不能證明自己獲得重生的人,仍然可以獲得成員資格上的接納。但是到18世紀初,他們才可以被聚會所接納。
14 可以列舉舊文獻中的一些資料(它們在德國不太為人所知)。Vedde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aptists (2nd ed. London, 1897)提供了浸禮會歷史的梗概;關于Hanserd Knollys:Culross, Hanserd Knollys, edited by P. Gould (London, 1891), vol. II(浸禮會手冊卷)。
關于再洗禮派的歷史有:E. B. Bax, Rise and Fall of the Anabaptists (New York, 1902);關于Smyth:Henry M. Dexter, The True Story of John Smyth, the Re-Baptist (Boston, 1881), 這是他本人和同時代人的敘述;一直以來都被引用的關于Hanserd Knollys社團的重要出版物(這是由J. Hadden為社團所付印的,Castle Street, Finsbury, 1846-54);還有官方的文獻見于The Baptist Church Manual by J.Newton Brown, D.D. (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shing Society, 30 S. Arch Street)。關于貴格派,除了Sharpless所引的著作,還有:A. C. Applegarth, The Quarkers in Pennsylvania, series X, vol. VIII, IX,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與政治科學研究系列;G. Lorimer, Baptists in History (New York, 1902); J. A. Seiss, Baptist System Examined (Lutheran Publication Society, 1902)。
關于新英格蘭(除Doyle外)的有:馬薩諸塞歷史匯編;此外還有Weede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1620-1789, 2 vols. Danial W. Howe, The Puritan Republic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關于舊的長老派之“誓約”觀念的發展,它的教會紀律,還有其與官方教會的關系,及與公理會和其他教派的關系,可見:Burrage, The Church Covenant Idea (1904)與The Early English Dissenters (1912);此外還有,W. M. Macphail,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918);J. Brown, The English Puritans (1910);Usher, The Presbyterian Movement, 1584-89 (Com. Soc., 1905)是重要的文獻。我們此處所給出的乃是與我們[研究]相關的非常隨機性的列舉。
15 前面提到的Bunyan有一個“Mr. Money-Love”的看法,即認為人們會為了獲得財富而變得虔誠,尤其是為了得到更多的贊助,這在十七世紀被認為是非常理所當然的;對于人們為什么會變得虔誠,這應是無關緊要的。(Pilgrim’s Progress, Tauchnitz ed., p. 114)
16 Thomas Clarkson, Portraiture of the Christian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London, 1867), p. 276.第三版(首版出于1830年左右)
17 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18 資料來源是茨溫利的論述:Füssli I, p. 228, cf. also pp. 243, 353, 263; Elenchus contra catabaptistas, Werke III, pp. 357, 362. 在其聚會中,茨溫利很典型地遇到了反對嬰兒受洗論者的困擾。這些人認為根據圣經,洗禮派的“分離”(因而也是意志論者)是令人反感的。布朗派在1603年向詹姆士國王進行了請愿,要求將所有“邪惡的撒謊者”從教會中驅逐出去,只接受“信仰者”和他們的孩子。但是長老會(大約)于1584年的教會統治的備忘錄(其原件第一次發表于A . F. Scott Pearson在海德堡的Ph. D論文,1912)則在第37款要求,只有服從紀律的人,或是(以別的方式表達其見證)者才可以被聚會所接納。
19 教派的自愿主義原則在本質上是有爭議的,它在邏輯上是遵循改革派教會(加爾文主義者)基于ecclesia pira的要求而來的。就如教派紀律所反對的那樣,這一教義原則現代在Kuyper(后來以第一執事而出名)那里是非常明顯的。他最后的一篇文章的標題就特別明顯地顯示了這一立場:Separatie en doleantie (Amsterdam, 1890)。他將此問題歸因于在非天主教基督教中,沒有永不謬誤的教義機構。這一教義斷言,看得見的教會的“軀體”并非舊的改革派教會之“圣體”(Corpus Christi),不過它在時間和空間上一定是保持分裂的,人性的弱點也一定保持了其對此的特性。一個可見的教會就信眾、及基督賦予他們的權威而言,其僅僅源于“一種意志的行為”(an act of will)。所以,抗議宗教會(potestas ecclesiastica)既不屬于基督本身,也不屬于執事(ministri),而僅僅屬于信眾團體。(在此Kuyper跟隨了Vo?t的立場)更大的共同體源于聚會者基于法律和自愿的聯合。
不過,這種聯合體一定是一種宗教的義務。根據羅馬的法令,這種聯合體是被拒絕的,因為教會成員只被允許出于他所處的本地社區的教區之中,他僅僅是一個eo ipso成員。浸禮只是賦予了他一種是純粹消極而不完全的角色(membrum incompletum),而沒有賦予他任何權利。在法律意義上,不是浸禮,而僅僅是belijdenis en stipulatie(信仰的歸依與善良意志的表白)授予了團體的成員資格。成員資格本身是要服從于教會紀律的(disciplina ecclesiae這也是Vo?t的立場)。教會法被相信是用來對付看得見的教會的那些人為的規則的,而那些規則,雖然和上帝的秩序相聯系,但并不代表上帝的秩序本身。(cf. Vo?t Pol. Eccles. vol. , pp. I and II)
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改革派教會中真正的根本法的獨立派因素,它們暗示出聚會團體(因而也是平信徒的)在接收新成員方面的一種積極性參與形式。(Von Rieker將這些法描述得很好)整個聚會團體的合作成員也構成了在新英格蘭的布朗獨立派(Brownist Independents)的重要一環。他們堅持這些立場,并強烈的反對冉森派(Johnsonist)的成功發展,后者堅持教會要受“長老”的統治。只有“改過重生者”才會被接納(根據Baillie,這些人是“四十個人才出一個的”)。在十九世紀,蘇格蘭獨立派的教會理論也差不多這樣看:只有通過特殊的方式才能獲得教會的接納(Sack, loc. cit.)。不過,Kuyper的教會理論在本質上當然并非是“會眾制”(congregationalist)的。
根據Kuyper的看法,個體的聚會在宗教上是有義務向作為整體的教會靠攏并屬于它的。在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個合法的教會。只有當“抗議”失敗時,這種歸屬的義務才會消失,分離的義務才會出現,也就是說,必須通過積極的抗議、消極的破壞等努力,以使得不好的教會得到改善(doleeren意為抗議,從技術上來說出現于17世紀)。最后,如果所有的努力都被證明無效的話,強制的做法興起,而分離也就成為一種義務。當然,如果是那樣的話,一個獨立派的憲章也是有必要的,因為在教會中沒有了“主題”,并且也因為信眾在本質上擁有神授的地位。革命可以是對神的一種義務(Kuyper, gekomen, pp. 30-31)。Kuyper(像Vo?t一樣)采納了一種久的獨立立場,即認為只有那些通過參與圣餐而被接納者,才是教會的真正成員。只有后者才能夠在浸禮期間承擔其孩子的委托權利。在神學意義上,一個信仰者就是一個內在的歸依者;而在法律意義上,一個信仰者僅僅是一個被接納參加圣餐儀式者。
20 對于Kuyper來說最基本的前提是,不把不信者的宗教聚會團體清除就是一種罪。(Dreigend Conflict, 1886, p. 41;參考Cor.11:26-27, 29; 1 Tim. 5: 22; Apoc. 18: 4.)但另方一方面在他看來,教會永遠無法判斷“在上帝面前”的恩典的狀態――與“Labadists”相對(屬激進的虔敬派)。不過就圣餐的接納而言,只有信仰和行為才是決定性的。十六、七世紀時荷蘭宗教會議在處理如何參加圣餐的先決條件上爭論不休。例如,1574年荷蘭南部的總教會議同意,如果沒有有組織的聚會的話,就不應當發放圣餐。長老與執事要小心注意,不讓沒有資格的人獲得接納。1575年的鹿特丹會議作出結論,所有在生活中犯有明顯過錯者不應被接納。(決定接納與否的不僅是牧師,還有長老們,那些提出這些反對意見的團體幾乎總是對牧師們更為寬松的政策持反對立場。如可參見Reitsma所引的例子[vol. II, p. 231])
圣餐接納的問題包括了以下的方面:關于一個再洗禮派教徒的丈夫能否被圣餐接納,在1619年于萊頓的宗教大會作出了決議,見第114款;倫巴第族的仆人能否獲得接納,1595年在Deventer的省級會議上作了決議,見第24款;那些宣布破產者能否接納,見1599年在Alkmaar的會議第2款,還有1605年會議的地28款;還有關于已經建立了協議的人也應被接納,1618年Enkhuizen的北荷蘭大會,Grav. Class. Amstel.第16條。后一種情況在以下情況是得到肯定回答的,只要宗教法院(consistorium)發現,[候選人]具有足夠的財產,并斷定他能保證債務人和家人都有足夠的衣食供應,那么就可以了。尤其是當債權人自己也對此協議很滿意,且債務人在未能履行義務的情況下進行悔罪,那就更是如此。有關倫巴第人的非準入資格,可見上面。為了避免爭執,配偶是被排除在外的,Reitsma III, p. 91。準入的另一個先決條件是,各個派別的法律爭執得到和解。對于長久的爭執,他們必須拿到聚會之外去[解決]。那些洗清了名譽的損害且對此一直有興趣者,也可以獲得有條件的接納。見同上,p. 176。
很可能是加爾文在法國移民的斯特拉斯堡聚會團體中第一個要求,要把那些其行為沒有令人滿意地通過考試的人從圣餐中排除出去。(不過后來不是該團體,而是執事大臣作出了該決定)根據真正的加爾文教義(Inst. Chr. Rel. IV, chap. 12, p. 4),除名的做法在法律上只能被運用于責難。(如在前述場所,除名被認為是頒布一項神圣判決)但是在同一地方(cf. p. 5),它也被視為一種“改進”的手段。
今天在美國,至少在都市地區,在浸信會中正式的除名還是很少見的。在實踐上,實行的是“退出”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某人的名字被簡單地且謹慎地從記錄當中劃掉。不過,在教派和獨立派當中,平信徒已經是紀律的典型承擔者了;而在最初的加爾文主義的長老派教會中,紀律是明顯而系統性的試圖要統治國家和教會。但是,在教會治理的階層和高級官員的問題上,甚至1854年英格蘭長老派的“備忘錄”(p. 14, note 2)也提倡由平信徒長者和執事們來擔當。
長老們和聚會團體的關系在不同情況下是有所不同的。就像(長老派的)長期國會把從圣餐中開除的決定權轉交到(平信徒)長老之手一樣,新英格蘭地區1647年的Cambridge Platform也與此類似。但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蘇格蘭獨立派還是把錯誤行為的公告交付一個委員會處理。在該委員會作出通告后,整個團體才作出開除的決定,這是一種對所有個人的關連義務更為嚴格的立場。這在前述布朗派的告白中也有反映,它是于1603年提交給詹姆士一世的(Dexter, loc. cit., p. 303),而“冉森派”則認為(選舉出來的)長老的統治是符合圣經的。長老們甚至可以與團體的決議相對,而行使開除的權利(如對Ainsworth的分離事件)。想了解早期的英格蘭長老會中的相關情況,可參見在前面注解4中所引的文獻,還有注解7中所引Pearson的博士論文。
21 順便說一下,荷蘭的虔敬派也相信這一原則。例如,Lodensteijn持這樣的觀點,人們必須同沒有重生的人相處;后者對前者來說很明顯是無重生跡象者。他甚至反對給孩子們談主禱(Lord’s Prayer),因為他們還沒有變成“主的孩子”。在尼德蘭,Kahler有時候還會見到這樣的觀點:重生者根本不會犯罪。在較小的中產階級下層群體中,確實可以見到正統的加爾文主義教義和令人吃驚的圣經知識。由于不相信神學教育和面對1852年的教會規定,正是正統派人士作出這樣的抱怨,平信徒在宗教大會中是缺乏充分的代表性的(除此之外還缺乏足夠嚴格的censura morum)。那時候德國正統的路德派教會還是不這樣看的。
22 轉引自Dexter, Congregationalism of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as Seen in its Literature (New York, 1880), p. 97.
23 伊麗莎白時代的英長老會希望認可英格蘭教會的39款規定(不過對34至36款保留,它們在此無關緊要)。
24 在十七世紀,從地方聚會團體中的非定居的浸信會眾所開出的介紹信是被圣餐接納的先決條件。非浸信會眾只有在經過團體的考察并得到認可后,才能被接納。(Hanserd Knollys Confession 1689年版的附錄,West Church, Pa., 1817)對于合資格的成員來說,參與圣餐是一種必需的義務。如果沒有加入到合法組織的本地聚會團體中,那就會被認為是分離主義。就帶有其他團體的必需的共同體而言,浸信會眾的觀點與Kuyper的看法(cf. above, note 8)相似。不過他們不承認有高于個別教會的任何司法權威。想了解訂立盟約者與早期英格蘭長老會眾的(介紹信),可見注解7和?中所引的文獻。
25 Shaw, Church History under the Commonwealth, vol. II, pp. 152-65; Gardiner, Commonwealth, vol. III, p. 231.
26 布朗派(Brownist)甚至在1603年向國王詹姆士對此請愿抗議。
27 例如,這一原理在1585年Edam的一個宗教會議的相似決議中得到表達。(見Reitsma系列,p. 139)
28 Baxter, Eccles. Dir., vol. II, p. 108在細節上討論了那些受到可疑的成員從聚會的圣餐中狼狽離去的場面(其根據是英格蘭教會的第25款)。
29 預定論的教義在此得到最純粹的表達。那些受到指責的孩子在其得到可靠證明后是否可以接受洗禮呢,此一表達對于這一問題是有著無比的關系和實踐重要性的。不過,預定論教義的實踐重要性還是一再受到不公平的質疑。在阿姆斯特丹難民的四個團體中,有三個贊同接納這些孩子們(十七世紀初);但是在新英格蘭,只有1657年的“Half-way Covenant”在此問題上作了放松。關于荷蘭的情況,見注解9。
30 Loc. cit. vol. II, p. 110.
31 還在十七世紀初,對非國教徒聚會的禁令就已經在荷蘭導致了一場普遍的“文化戰爭”(Kulturkampf)。伊麗莎白對非國教徒的聚會義非常粗暴的手法加以反對(在1593年加以罰款的威脅)。在此后面的[真正]原因是禁欲主義者宗教上的反權威主義性格,或者更確切的說,在宗教和世俗權威之間有競爭性關系(Cartwright曾明確下令,即使是親王也得以被除名)。事實上,蘇格蘭的例子就必然有威懾性的影響,那里的長老派教會紀律之階級土壤和神職人員統治站在了國王的對立面。
32 為了避開正統牧師的宗教壓力,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公民吸取了自己的教訓,曾把他們的孩子送到相鄰的聚會團體中去。阿姆斯特丹團體的Kerkraad教會理事會(于1886年)拒絕承認由這些執事所制定的成員之道德行為的資格證書。這些成員被從圣餐中排除,因為團體必須要保持其純潔性,也因為必須服從主(而非人)。當宗教大會委員會贊同對這種分離行為否定的做法時,教會理事會拒絕服從和采納新規則。根據后者,教會理事會的拒絕給了自己超越于教會之上的獨一無二的授職權。這就拒絕了帶有宗教會議的社區,并將(平信徒)長老們架空了,T. Rutgers與Kuyger為Nieuwe Kerk[New Church]之詭計所困,盡管前者的看護人中也有后者。(Cf. Hogerfeil, De kerkelijke strijd te Amsterdam, 1886,此外還有前面提及的Kuyger之著作)
在1820年代,預定論運動就已經開始了,領導者為Bilderdijk和他的弟子Issac da Costa及Abraham Capadose(兩個受洗的猶太人)。(因為預定論的教義拒絕某些東西,例如像拒絕種痘那樣拒絕把廢除黑奴作為對羅德州事務的干涉)他們滿懷激情地為放松教會紀律而戰斗,并對不合格者準入圣事。這一運動導致了[教派]分離。1840年,阿姆斯特丹的“Afgeschiedenen gereformeerten Geemeente”(分離的改革派團體)接納了Dorderecht Canouns,并拒絕了任何一種“在教會之內或之上”的支配形式。Groen van Prinsterer是Bilderdijk的門徒之一。
33 1611年在“Amsterdam Confession”中建立了古典的規則陳述(Publ. of the Hanserd Knollys Society, vol. X)。故而,第16款這樣規定,“每一教會與團體的成員都應該相互認識……所以一個教會不應建立在數量的基礎上,使各成員彼此不知悉。”故而在最新的情況中,任何宗教大會的規則與任何中心教會的權威之建立都被視為原則上的叛教。這在馬薩諸塞州出現了,而且就像克倫威爾治下的英格蘭。這些規則是議會在1641年建立起來的,在那時它們允許每一個團體為自己準備一個傳統的執事,并組織演講。這一手段導致了浸信會成員的流失和激進的獨立派的出現。早期的長老會Dedham協議(由Usher發表)也預示了這一點,肯定對個別團體(在那時事實上最可能是個別執事)是教會紀律的承擔者。在1582年10月22日的協議中明顯的是以投票表決是否接納,“沒有全體的普遍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帶入到任一群體中。”不過早在1586年,這些接受了公理會原則的清教徒就宣布,他們反對布朗派成員的加入。
34 循道宗的“班”――以靈魂的合作治療為基礎――乃是整個自制的脊梁骨。每十二人就組成一“班”。班的領導者在每周都要拜訪每個成員,要么在家里,要么在班聚會中,在此他們通常要對罪作出普遍的懺悔。領導者要對每一個成員的行為作出記錄。在其他情況下,這些書面記錄將決定那些離開了本地社區的成員的書面資格。到目前為止,很長時間里,這種組織在每個地方都一直處于瓦解狀態,包括美國。從前引Dedham協議可以看出,早期的清教主義之紀律就是此種方式運作,據此在非國教徒聚會中“如果有任何事情被弟兄看到或觀察到”,要給予“警告”。
35 在路德派的地盤,尤其是德國,教會紀律不是糟糕地毫無發展,就是在早期就已經被徹底耽誤了。在德國的改革派教會里,教會紀律也是只有微不足道的影響,只有Julich-Cleve和其它萊茵地區例外。這要歸因于路德派外部環境的影響,還有在國家權力和競爭性、自主性等級力量之間的相互妒忌。這種妒忌無處不在,不過國家在德國過去還是一直有無上的權力。(雖然如此,教會紀律直到十九世紀才建立起來。最近的一次除名發生在1855年的諸侯領地上。但是,1563年的教會規則從早期開始,就一直以一種實際上是國家全能主義的方式被操控著。) 只有門諾派和后來的虔敬派產生了有效的紀律約束手段,即相關的組織。(對門諾來說,一個“可見的教會”僅僅存在于有教會紀律存在的地方。由于不當行為和混亂的婚姻會造成除名,這在這些紀律中是一個自明的要素。Rynsburg Collegiants沒有什么教理,只是根據“行為”來判斷。)在胡格諾派(Huguenots)之中,教會紀律本身是非常嚴厲的,不過通過不可避免的高貴性的考慮(這在政治上是必不可少的),嚴厲的紀律被一再放松。
清教教會紀律在英格蘭的擁護者尤其見于資產階級化的中等階級中,即如,倫敦市的中等階級。城市不擔心神職人員的統治,反而希望把教會紀律作為大眾生活的一種方式。工匠階層也非常支持教會紀律。政治權威則是教會紀律的反對者。故而在英格蘭的反對者也包括了議會。瞟一下每一個文件就可以看到,在此有影響的因素并非“階級利益”,而是基本的宗教利益與理解,此外還有政治的。不僅在新英格蘭,而其在歐洲的真正的清教教會都是出名的嚴苛。在克倫威爾的major-generals和委員中,為了推行教會紀律,他的代表們提出要驅逐所有“懶散、荒淫和瀆神的人”,這樣的動議被一再地提出。
在循道宗中,新手在受罰期間推出是被允許的,無需更多糾纏。老資格的成員的退出要經由一個委員會的調查之后才行。胡格諾派(它很長時間實際上都是一個“教派”)的教會紀律在宗教會議的協議中可以見到。在其他方面,這些東西顯示出可以擔保沒有貨物摻假和商業欺詐行為。(見Sixth Synod,Avert. Gen. XIV)故而反奢侈的法律是針對財政普遍比較緊的情況而實行的(fiscus是一個暴君),見Sixth Synod, cas de conc. dec, XIV;關于高利貸,見同上XV(cf. Second Synod, Gen. 17; Eleventh Synod, Gen. 42)。到了十六世紀末,英國長老會眾在官方通信中被稱為“紀律主義者”。(引文見Pearson, loc. cit.)
36 幾乎在所有教派中,都有一段見習期。如在循道宗中,為期六個月。
37 在威斯敏斯特宗教大會上的五個(獨立派)“反對派兄弟”中的“Apologetical Narration”中,從那些“不堅定和形式上的基督徒”中分離出來的問題被置于首位。這首先意味著這只是一種自愿式的分離,而非一樁交易。但是羅賓遜,一位嚴厲的加爾文主義者和Dordrecht大會的擁護者(關于他見cf. Baxter, Congregationalism, p. 402),最初持這樣的觀點(后來有松動),獨立派分離主義者不一定要和其他人做社會交流(即便他們是被選舉出來的),這被認為是可以理解的。盡管如此,大部分教派都避免讓自己明顯地與這種紀律掛鉤,有些則明白地拒絕它,至少在原則上是如此。巴克斯特(Christian Directory, vol. II, p. 100之第二欄的底端)以為,如果不是本人而是家長與郊區牧師承擔了責任的話,那么這個人就等于默許了與一個無信仰的人共禱。不過,這是非浸信會的[立場]。在荷蘭17世紀激進的浸禮會教派中,這種mijdinge(中間物)扮演著一個極重要的角色。
38 在17世紀初的阿姆斯特丹難民團體中,甚至在其內部的爭論與斗爭中這一點就已變得非常明顯。就如在蘭開夏郡對一個“執事”(ministrial)教會紀律的拒絕一樣,在教會中要求有一種平信徒準則和由平信徒執行的紀律,這一要求是因著克倫威爾時代的教會內部斗爭的態度而做出的。
39 長老的任命乃是在獨立派和浸禮會社群中長期討論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此與我們無涉。
40 1646年12月31日長期國會的條例被用來反對這個。它被視為對獨立派的一個打擊。另一方面,預言自由的原則也已為羅賓遜以書面形式所論證。Jeremy Taylor從主教制的立場出發對此作了讓步(The Liberty of Prophesying, 1647)。克倫威爾的“嘗試”這樣要求,只有在團體中得到六個合格的成員(中間要有四人為平信徒)的授權下,預言才是被許可的。在英國教會改革的早期,熱情的安立甘宗主教不僅經常容忍“練習”與“預言”,而且還對此加以鼓勵。在蘇格蘭,這些是教會活動的要素;在1571年它們又被引入了北安普頓。其它一些地方很快也跟隨之。但是伊麗莎白一直壓制它們,其結果就是她1573年反對Cartwright的聲明。
41 阿姆斯特丹的史密斯已經做出了這樣的訴求,在祈禱重生的時候,在他面前甚至不能有圣經。
42 在這些團體中,(Fox與相似領導一類型的)宗派主義者卡里斯瑪革命的開端往往是反對作官方控制的“薪俸階層”,為自由布道的使徒原則而戰,對于被圣靈所感動的講者來說是不需要報酬的。在Godwin這樣的會眾制的擁護者和Prynne這樣批評他的人之間,在國會中產生了激烈辯論,這一辯論反對他所宣稱的原則、他所曾經承認的“生存方式”;盡管如此,Godwin宣布只承認自愿提供的原則。只有對于執事的維持做出的自愿貢獻才應該被承認,這一原則在布朗派向詹姆士一世的請愿中得到了表達。(第71點:所以有對“教皇式生計”和“猶太教式宗教稅”的反對)
43 在1649年5月1號的人民協定(Agreement of the People)中,后者是對所有牧師都要求的。
44 故而循道宗的地方牧師就是如此。
45 在1793年循道宗廢除了授職和非授職的牧師之間的區分。由此,非授職的巡回牧師,當然還有布道團(他們是該派的重要特征),這兩者從此與圣公會所授職的牧師處于同等社會地位。但是與此同時,只有巡回牧師得到了巡回布道和圣事管理的壟斷權力。(圣事的自主管理主要通過他們來處理,但是與那些其成員準入資格裝得與以前一樣的官方教會的管理相比,也有段時間不同)在1768年以來,禁止牧師擔任普通的中產階級職位,于是一個新的“神職階層”產生了。
46 事實上,至少在英格蘭,大部分的“巡回團”都幾乎沒有什么教區,牧師的流動幾乎成了一個虛幻。不過雖然如此,到目前為止還堅持這一點,即同一個執事不能在同一個巡回團中服務超過三年。他們是職業牧師。不過,“本地牧師”(巡回牧師是從他們中間招募的)是一些有中產階級職位的人,并且擁有講道的執照,有一段時間這一執照原本只被授予一年。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因為禮拜與侍奉的位子太多了。但是首先,他們是“班”(組織)和靈魂治療的中堅。所以,他們乃是教會紀律[維持]的中心器官。
47 在其它問題上,克倫威爾對“圣徒國會”(Parliament of Saints’)的反對成為了大學的一個敏感問題。(在大學中所有什一稅都被徹底廢除,薪俸層[教牧]也消失了)盡管這樣,克倫威爾無法廢除這些文化機構,對于神學教育來說尤其如此。
48 在此根據1652年的規議,本質上也是根據1654年的教會憲章。
49 Gardiner給出了一個例子,見Fall of Monarchy, vol. I, p. 380。
50 威斯敏斯特懺悔(Westminster Confession)也(XXVI, I)建立了互相幫助的內外義務之原則。在所有教派中都有很多這樣的規則。
51 循道宗經常試圖以開除來懲罰那些訴諸世俗司法的人。另一方面,在某些例子中,他們也會建立某種權威機構,如果債務人不肯還錢,他們就會訴諸于此權威。
52 在早期的循道宗,沒有付薪的每一個案例都要被一個弟兄委員會所調查。因不能付報酬而導致債務是會招致開除的,這也是建立信用評級的方式。(Cf.見注解9中所引荷蘭宗教大會的決議)幫助處于危難之中的弟兄是被要求的,例如在Baptist Hanserd Knollys Confession(c. 28)中就保留如此特征,不過這并不至于對財產的神圣性產生偏見。偶爾地,也是非常嚴肅的(就如在1647年Cambridge platform中那樣,見edition of 1653, 7, no. VI)長老們被提醒他們的責任是反對那些“沒有天職”生活的成員,或是“惰于其天職”行為的成員。
53 循道宗就有這樣的表述。
54 在循道宗中,這些行為的認證最初每三個月就更新一次。舊的獨立派,就如前面指出的那樣,只給持證者授予圣餐。在浸禮會中,一個新加入社區者必須要有其原來的聚會團體的介紹信才能被接收。(cf. the appendix to the edition of the Hanserd Knollys Confession of 1689, West Chester, Pa., 1827)甚至16世紀初的阿姆斯特丹的三個浸禮會群體就已有了相同制度,從此以后它在每一地方都產生了。在馬薩諸塞州是1669年開始,資格證是從牧師和關心正統教義及行為的選民那里發出的,它可以證明持有者是有資格獲得政治公民身份的。這一資格證最初是用于行使圣餐準入功能的,后來也就代替了后者。
55 我們前面一再引用過道利(Doyle)的著作,他把新英格蘭地區與農業殖民地相對的工業化特征也歸因于此。
56 例如,道利談到了新英格蘭地區的地位狀況,那里構成貴族的不是“有產階級”,而是承擔著舊的宗教文本傳統的家庭。
57 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58 我們還要重點強調兩文(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首篇中的絕對定論。沒有將這一事實公布出來是我的評論家們的基本錯誤。在討論和埃及、腓尼基和巴比倫的倫理體系中的交易相關聯的古代希伯來倫理時,我們處在一個非常相似的位置上。
59 Cf.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66頁的其它評論中。在古猶太民族聚會團體的形成中,和古代基督教一樣,在相同的大方向上各自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如我們所看到的,在猶太民族中,對親緣的社會重要性的拒絕是其條件,故而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中也有類似的影響)
60 Cf. The Livre des Métiers of the Pré? ?tienne de Boileau of 1268 (éd. Lespinasse & Bannardot in the Histoire Gégérale de Paris) pp. 211, sect. 8; 215, sect. 這方面可能還有許多其它的例子。
61 在此我們不能分析這種相當偶然涉及的關系,只能一筆帶過。
(引自中國藝術批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