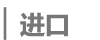東盟各國是中國構建亞太經濟共同體的“左鄰右舍”。近年來,雙方經貿合作不斷深化,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取得顯著成績。然而,過去兩年,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蔚藍大海并不平靜。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不斷推進,自貿區升級在交通通信、金融合作、機制完善等領域面臨諸多挑戰。
伴隨著緬甸內亂、越南人對中國企業的打砸事件,公眾對與東盟國家開展外經外貿多了一份擔心。最近,中國貿易報社新聞采訪團到達中緬、中越邊境,考察了邊貿企業發展情況。一路前行,記者發現在邊境上生活的人們想得開,邊貿企業也“走得出去”。
依靠中國與東盟經貿發展生存的企業到底圖什么、求什么?在深入了解了一些與東盟國家有深入接觸的邊貿企業的“苦與樂”之后,采訪團推出本期報道,以饗讀者。
做什么?
很多企業給出的答案大致相同,天生友鄰,有成本優勢。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實施了沿邊開放政策,邊境貿易迅速發展,國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文件,極大地促進了邊境地區的對外開放。在這一過程中,很多有先天地理優勢的邊境企業隨著邊境貿易的發展而成長壯大。
有政策扶持、成本僅國內一半、投資回報高、迅速致富,這是很多中國企業發展邊貿、投資東盟的理由,在緬甸搞種植的騰沖金鑫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騰沖金鑫)同樣如此。
“西雙版納每畝香蕉地的租金是3000元,但緬甸每畝地的租金僅為400元。而且,種植香蕉所需的人工費用在國內最少也是每人每天200元,但在緬甸雇傭小工種植香蕉,每天的工錢折合成人民幣最多只要20元。”騰沖金鑫總經理劉天益告訴記者,“緬甸有大量肥沃的土壤且地租便宜,能夠進行規模化種植。”
由于這些“優惠”,劉天益在緬甸種香蕉的成本比國內低了很多。此外,他還告訴記者,由于土地肥沃,在緬甸種植,用肥、用藥都是相當少的,用量和花費都會減半。
巨大的內部市場、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為資本、商品和勞務的跨國流動帶來較大的便利和商機。其實,在邊境,很多中國企業最開始還只是從鄰國進口產品。但隨著交往日益密切,邊貿企業發現,到進口國投資設廠,不僅能減少成本,生產出來的產品品質也更好,而借由對外投資,企業更貼近當地市場,還能開拓出更廣闊的經營區域。借著這些“誘人”的引資優勢,東盟國家吸引到大量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
而除此之外,天生友鄰的地理優勢也讓不少企業更加倚重在邊境線上做生意。這也符合常理。一般來說,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初期的區位選擇通常都要遵循“就近原則”和“地區漸進原則”,因為對鄰近國家的投資可以使經營風險一定程度地降低。中國與越南、老撾和緬甸三國直接接壤,與其他東盟國家也是近鄰,擁有相互投資的地緣優勢。
大海糧油工業(防城港)有限公司飼料部專業副總監王偉就告訴記者,該公司之所以選擇防城港作為“駐地”,是看中防城港面朝大海、輻射西南的地理位置。
背靠大西南、面向東南亞、南臨北部灣的防城港西南與越南接壤,海岸線長達580公里,陸地邊界也有100多公里。其所轄東興市,市區與越南芒街市相隔一條數十米的北侖河,市內幾乎每家每戶都做對越生意,而且都有自己多年來形成的交易線路。做海產品進出口貿易的怡誠食品公司就把“家”安在了東興。該公司董事長助理石先生說,區位優勢不可忽視。
2012年,東興邊境貿易進出口成交額為192.23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35%,其中邊境小額貿易進出口成交額為35.9億元,互市貿易進出口成交額為156.33億元。
要什么?
對于外貿企業來說,最缺的無疑是兩樣——資金和配額。
中國一直支持企業“走出去”,用經濟作物替代緬甸等地的罌粟種植。去緬甸等東盟國家種植,背后不僅有利益驅動,也有國家政策扶持。但是,問題隨之而來。替代種植面積在迅速擴大后,返銷配額則開始收緊。
“雖然國家各項政策對我們在緬甸投資給與了不少支持和幫扶,但在分配進出口指標時卻有偏重。我們在緬甸種植農產品,只有10%至20%的產品能夠通過返銷配額銷往國內,剩余的產品只能在政府的引導下通過邊貿互市的方式消化,企業要自己承擔的壓力很大。”劉天益表示。
為此,騰沖縣市商務局急企業所急,積極向上級機關反映情況,為替代企業爭取名額,但效果并不明顯。
“騰沖為企業返銷配額不夠而著急,但這一指標是省商務廳統一分配的,下放到各縣,要均衡分配。”騰沖縣商務局副局長劉品成無奈地對記者說。
而除了配額問題,讓企業撓頭的還有資金。
曾有業內人士分析,銀行給邊境進出口企業放款是有很多擔心的。一方面,進出口公司往往都是代理業務,提供的材料復雜、難以核實,而且很多沒有資質的公司會掛靠有資質的公司來融資;另一方面,越南、老撾、緬甸商人結算較慢,有時故意拖欠,也會發生因為匯率不劃算而改變付款期等情況,交易周期完成時間不可控,風險較大,目前銀行適合的融資產品很少。
云南騰沖興華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興華貿易)是騰沖供銷社下屬的一個商行,2000年改制為私營,主營業務除了進出口產品,還幫助伙伴企業發展對外貿易。“我們公司還算有規模,所以銀行愿意貸款給我們,但是,我們有一些小的合作企業,他們的境況不同了。”該公司總經理楊黎說。
隨著貿易流通速度的加快,進出口公司在資金周轉方面面臨更大的挑戰。不少邊貿企業處于有伙伴、有項目,卻苦于資金缺乏而無法運作的狀態,這種狀況既限制了企業的發展,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縮小了銀行的業務范圍。
而除了貸款,匯率的波動也給企業帶來很大困擾。
“邊境還是以民間銀行和現金結算為主,稅率波動比較大。而按照緬甸國內的匯率,100美元等于1500緬幣,但是人民幣兌換成1500緬幣也就十來塊錢。按照央行規定的匯率,企業損失很大。”楊黎說。
可喜的是,國家早就對匯率問題有所關注。據記者了解,很多設立在邊境的銀行都有貨幣兌換交易業務,國家也對匯率波動有所把控。
愁什么?
如果外貿互聯互通不暢,帶給企業的影響是無法預估的。
即便是企業在國內已經搞定一切,資金、人力、物力等均已齊備,但在進行貿易往來時,這些企業還是會遇到其它“煩心事”。而作為邊貿企業,最常見的問題是交通不暢。
隨著中國邊境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區域貨物人員流通量也急劇增加,對于交通便利化建設的進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在很多地區,互聯互通和貿易往來卻處于“通而不暢”的狀態,貿易貨物運輸、人員交往成本較高成為邊貿發展亟待突破的瓶頸。
記者在北侖河二橋工程現場看到,該工程中國段已經開始等待對接。而遙望越方的工程現場,崎嶇不平的泥土地顯示了工程處在停滯狀態。據知情人士介紹,中方的工程一直在有序推進,但隸屬于越方的工程進展緩慢,導致整個工程的進度不統一,目前看來,中越工程對接無望。
據記者了解,近年來,中國投入大量資金推動邊境交通運輸建設,但由于中國與領國間的客貨運輸協定還不完善,部分區域的物流交通建設呈現出“半邊紅”的狀態。
不僅是交通建設受阻,東盟一些國家境內運輸條件較差,也增加了企業的進出口運輸成本,高額的通關費用更是讓不少商貿企業望“路”興嘆。
楊黎就對記者表示:“緬甸邊境地區民族獨立武裝控制的區域,不斷會有人出來收取過路費,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對于商人來說,雖然是破財免災,但無形中提高了貿易風險和商家成本。”
劉天益的生意做得更大。騰沖金鑫能夠在緬甸順利運貨,掌舵人劉天益憑借的是在當地廣闊的人脈。但即便是與緬甸中央政府官員和地方武裝首領均有往來,劉天益仍舊要投入上百萬元的“通關”費用。
“從騰沖國境線到緬甸密支那,短短100多公里的路上就有14道關卡,即便有正常的通關手續也需要額外打點。而在平時,更要不時地‘關照’一下口岸官員,煙、錢都是少不了的。緬方口岸管理人員每3個月更換一次,每次的收費標準也不一樣,而且是停車就收費。花錢還好,關鍵是耽誤時間。”對于緬甸濃郁的“人治”色彩,劉天益雖然無奈,但也只能接受并適應。
記者手記
西南散記之邊貿企業的智慧
走走看看聊聊,一路上,我們不斷與生活在邊境上的企業接觸。借助于地緣優勢,這些企業成為貿易企業里獨特的分支——邊境貿易企業,大量借助于貨車而非貨輪,將產品從國界一邊拉到另一邊。
很多邊貿企業從事進出口貿易,它們船小好調頭,企業掌舵人能夠發揮智慧謀求發展。當然,他們也有頗多無奈,本已一路坎坷經營,若再不幸遇到對方國家戰火紛飛,需要的就不光是商人的智慧了。
在中越關系越來越緊張的當下,筆者在邊境卻看到了一片祥和氣象。這得益于邊境貿易對該地區的促進作用。邊境貿易,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富民、安邦”的巨大作用,而一個個貿易公司,則是這堵厚墻上的磚瓦。
我們在采訪中了解到,多年的經營讓這些公司從業者身上多少帶了些傳奇色彩。他們不僅關心國人需要什么,也更關心能給鄰邦帶來什么。當然,鄰國的風吹草動,是這些人最為敏感的。由于緬甸、越南國內出現動亂或與中國關系緊張等給投資環境造成影響,這些生意人有了許多可“吐槽”的內容。
然而,“吐槽”歸“吐槽”,該做的生意依舊要做下去。對于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困境,他們的態度也很值得玩味。從兩國口岸通關是否便利到對方國內投資扶持政策、再到返銷配額等這些問題都需要“上面的人”的智慧,但是,對于似乎可以解決某些問題的方法——加強與緬甸、越南等東盟國家的會晤制度,他們卻只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在對方政權不穩的情況下,上傳卻無法下達,與其等待“上面人”動用智慧不如自己頭腦風暴一下。有家企業甚至已經做到,如緬甸出現交火會提前收到通知。但這里面所耗費的精力,我們也可想而知。
對于地方政府,邊貿企業還是愿意親近的。畢竟,大多國家對于邊貿的重視程度較高,基礎設施、優惠政策、融資等一系列與外經外貿的環節都被“特殊關照”。
因而,在政府主導下,基礎設施建設自然而然地繼續加大,尤其對于西南地區的道路建設、與邊貿配套的集驗貨、倉儲和交易為一體的市場建設更應被加大投入。對于邊境地區邊貿進出口商品的配額也應根據情況適時調整。依托口岸,以工業園區為平臺,引導貿易聚集形成規模,把邊境貿易加工基地建設成為集制造、出口加工、運輸、物流、倉儲為一體的邊境經濟合作區。其他方面,中國-東盟博覽會現在已經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交流平臺,利用博覽會,創造更多機會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伴隨著緬甸內亂、越南人對中國企業的打砸事件,公眾對與東盟國家開展外經外貿多了一份擔心。最近,中國貿易報社新聞采訪團到達中緬、中越邊境,考察了邊貿企業發展情況。一路前行,記者發現在邊境上生活的人們想得開,邊貿企業也“走得出去”。
依靠中國與東盟經貿發展生存的企業到底圖什么、求什么?在深入了解了一些與東盟國家有深入接觸的邊貿企業的“苦與樂”之后,采訪團推出本期報道,以饗讀者。
做什么?
很多企業給出的答案大致相同,天生友鄰,有成本優勢。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實施了沿邊開放政策,邊境貿易迅速發展,國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文件,極大地促進了邊境地區的對外開放。在這一過程中,很多有先天地理優勢的邊境企業隨著邊境貿易的發展而成長壯大。
有政策扶持、成本僅國內一半、投資回報高、迅速致富,這是很多中國企業發展邊貿、投資東盟的理由,在緬甸搞種植的騰沖金鑫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騰沖金鑫)同樣如此。
“西雙版納每畝香蕉地的租金是3000元,但緬甸每畝地的租金僅為400元。而且,種植香蕉所需的人工費用在國內最少也是每人每天200元,但在緬甸雇傭小工種植香蕉,每天的工錢折合成人民幣最多只要20元。”騰沖金鑫總經理劉天益告訴記者,“緬甸有大量肥沃的土壤且地租便宜,能夠進行規模化種植。”
由于這些“優惠”,劉天益在緬甸種香蕉的成本比國內低了很多。此外,他還告訴記者,由于土地肥沃,在緬甸種植,用肥、用藥都是相當少的,用量和花費都會減半。
巨大的內部市場、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為資本、商品和勞務的跨國流動帶來較大的便利和商機。其實,在邊境,很多中國企業最開始還只是從鄰國進口產品。但隨著交往日益密切,邊貿企業發現,到進口國投資設廠,不僅能減少成本,生產出來的產品品質也更好,而借由對外投資,企業更貼近當地市場,還能開拓出更廣闊的經營區域。借著這些“誘人”的引資優勢,東盟國家吸引到大量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
而除此之外,天生友鄰的地理優勢也讓不少企業更加倚重在邊境線上做生意。這也符合常理。一般來說,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初期的區位選擇通常都要遵循“就近原則”和“地區漸進原則”,因為對鄰近國家的投資可以使經營風險一定程度地降低。中國與越南、老撾和緬甸三國直接接壤,與其他東盟國家也是近鄰,擁有相互投資的地緣優勢。
大海糧油工業(防城港)有限公司飼料部專業副總監王偉就告訴記者,該公司之所以選擇防城港作為“駐地”,是看中防城港面朝大海、輻射西南的地理位置。
背靠大西南、面向東南亞、南臨北部灣的防城港西南與越南接壤,海岸線長達580公里,陸地邊界也有100多公里。其所轄東興市,市區與越南芒街市相隔一條數十米的北侖河,市內幾乎每家每戶都做對越生意,而且都有自己多年來形成的交易線路。做海產品進出口貿易的怡誠食品公司就把“家”安在了東興。該公司董事長助理石先生說,區位優勢不可忽視。
2012年,東興邊境貿易進出口成交額為192.23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35%,其中邊境小額貿易進出口成交額為35.9億元,互市貿易進出口成交額為156.33億元。
要什么?
對于外貿企業來說,最缺的無疑是兩樣——資金和配額。
中國一直支持企業“走出去”,用經濟作物替代緬甸等地的罌粟種植。去緬甸等東盟國家種植,背后不僅有利益驅動,也有國家政策扶持。但是,問題隨之而來。替代種植面積在迅速擴大后,返銷配額則開始收緊。
“雖然國家各項政策對我們在緬甸投資給與了不少支持和幫扶,但在分配進出口指標時卻有偏重。我們在緬甸種植農產品,只有10%至20%的產品能夠通過返銷配額銷往國內,剩余的產品只能在政府的引導下通過邊貿互市的方式消化,企業要自己承擔的壓力很大。”劉天益表示。
為此,騰沖縣市商務局急企業所急,積極向上級機關反映情況,為替代企業爭取名額,但效果并不明顯。
“騰沖為企業返銷配額不夠而著急,但這一指標是省商務廳統一分配的,下放到各縣,要均衡分配。”騰沖縣商務局副局長劉品成無奈地對記者說。
而除了配額問題,讓企業撓頭的還有資金。
曾有業內人士分析,銀行給邊境進出口企業放款是有很多擔心的。一方面,進出口公司往往都是代理業務,提供的材料復雜、難以核實,而且很多沒有資質的公司會掛靠有資質的公司來融資;另一方面,越南、老撾、緬甸商人結算較慢,有時故意拖欠,也會發生因為匯率不劃算而改變付款期等情況,交易周期完成時間不可控,風險較大,目前銀行適合的融資產品很少。
云南騰沖興華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興華貿易)是騰沖供銷社下屬的一個商行,2000年改制為私營,主營業務除了進出口產品,還幫助伙伴企業發展對外貿易。“我們公司還算有規模,所以銀行愿意貸款給我們,但是,我們有一些小的合作企業,他們的境況不同了。”該公司總經理楊黎說。
隨著貿易流通速度的加快,進出口公司在資金周轉方面面臨更大的挑戰。不少邊貿企業處于有伙伴、有項目,卻苦于資金缺乏而無法運作的狀態,這種狀況既限制了企業的發展,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縮小了銀行的業務范圍。
而除了貸款,匯率的波動也給企業帶來很大困擾。
“邊境還是以民間銀行和現金結算為主,稅率波動比較大。而按照緬甸國內的匯率,100美元等于1500緬幣,但是人民幣兌換成1500緬幣也就十來塊錢。按照央行規定的匯率,企業損失很大。”楊黎說。
可喜的是,國家早就對匯率問題有所關注。據記者了解,很多設立在邊境的銀行都有貨幣兌換交易業務,國家也對匯率波動有所把控。
愁什么?
如果外貿互聯互通不暢,帶給企業的影響是無法預估的。
即便是企業在國內已經搞定一切,資金、人力、物力等均已齊備,但在進行貿易往來時,這些企業還是會遇到其它“煩心事”。而作為邊貿企業,最常見的問題是交通不暢。
隨著中國邊境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區域貨物人員流通量也急劇增加,對于交通便利化建設的進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在很多地區,互聯互通和貿易往來卻處于“通而不暢”的狀態,貿易貨物運輸、人員交往成本較高成為邊貿發展亟待突破的瓶頸。
記者在北侖河二橋工程現場看到,該工程中國段已經開始等待對接。而遙望越方的工程現場,崎嶇不平的泥土地顯示了工程處在停滯狀態。據知情人士介紹,中方的工程一直在有序推進,但隸屬于越方的工程進展緩慢,導致整個工程的進度不統一,目前看來,中越工程對接無望。
據記者了解,近年來,中國投入大量資金推動邊境交通運輸建設,但由于中國與領國間的客貨運輸協定還不完善,部分區域的物流交通建設呈現出“半邊紅”的狀態。
不僅是交通建設受阻,東盟一些國家境內運輸條件較差,也增加了企業的進出口運輸成本,高額的通關費用更是讓不少商貿企業望“路”興嘆。
楊黎就對記者表示:“緬甸邊境地區民族獨立武裝控制的區域,不斷會有人出來收取過路費,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對于商人來說,雖然是破財免災,但無形中提高了貿易風險和商家成本。”
劉天益的生意做得更大。騰沖金鑫能夠在緬甸順利運貨,掌舵人劉天益憑借的是在當地廣闊的人脈。但即便是與緬甸中央政府官員和地方武裝首領均有往來,劉天益仍舊要投入上百萬元的“通關”費用。
“從騰沖國境線到緬甸密支那,短短100多公里的路上就有14道關卡,即便有正常的通關手續也需要額外打點。而在平時,更要不時地‘關照’一下口岸官員,煙、錢都是少不了的。緬方口岸管理人員每3個月更換一次,每次的收費標準也不一樣,而且是停車就收費。花錢還好,關鍵是耽誤時間。”對于緬甸濃郁的“人治”色彩,劉天益雖然無奈,但也只能接受并適應。
記者手記
西南散記之邊貿企業的智慧
走走看看聊聊,一路上,我們不斷與生活在邊境上的企業接觸。借助于地緣優勢,這些企業成為貿易企業里獨特的分支——邊境貿易企業,大量借助于貨車而非貨輪,將產品從國界一邊拉到另一邊。
很多邊貿企業從事進出口貿易,它們船小好調頭,企業掌舵人能夠發揮智慧謀求發展。當然,他們也有頗多無奈,本已一路坎坷經營,若再不幸遇到對方國家戰火紛飛,需要的就不光是商人的智慧了。
在中越關系越來越緊張的當下,筆者在邊境卻看到了一片祥和氣象。這得益于邊境貿易對該地區的促進作用。邊境貿易,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富民、安邦”的巨大作用,而一個個貿易公司,則是這堵厚墻上的磚瓦。
我們在采訪中了解到,多年的經營讓這些公司從業者身上多少帶了些傳奇色彩。他們不僅關心國人需要什么,也更關心能給鄰邦帶來什么。當然,鄰國的風吹草動,是這些人最為敏感的。由于緬甸、越南國內出現動亂或與中國關系緊張等給投資環境造成影響,這些生意人有了許多可“吐槽”的內容。
然而,“吐槽”歸“吐槽”,該做的生意依舊要做下去。對于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困境,他們的態度也很值得玩味。從兩國口岸通關是否便利到對方國內投資扶持政策、再到返銷配額等這些問題都需要“上面的人”的智慧,但是,對于似乎可以解決某些問題的方法——加強與緬甸、越南等東盟國家的會晤制度,他們卻只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在對方政權不穩的情況下,上傳卻無法下達,與其等待“上面人”動用智慧不如自己頭腦風暴一下。有家企業甚至已經做到,如緬甸出現交火會提前收到通知。但這里面所耗費的精力,我們也可想而知。
對于地方政府,邊貿企業還是愿意親近的。畢竟,大多國家對于邊貿的重視程度較高,基礎設施、優惠政策、融資等一系列與外經外貿的環節都被“特殊關照”。
因而,在政府主導下,基礎設施建設自然而然地繼續加大,尤其對于西南地區的道路建設、與邊貿配套的集驗貨、倉儲和交易為一體的市場建設更應被加大投入。對于邊境地區邊貿進出口商品的配額也應根據情況適時調整。依托口岸,以工業園區為平臺,引導貿易聚集形成規模,把邊境貿易加工基地建設成為集制造、出口加工、運輸、物流、倉儲為一體的邊境經濟合作區。其他方面,中國-東盟博覽會現在已經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交流平臺,利用博覽會,創造更多機會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