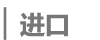⊙記者 王誠誠 ○編輯 于勇
或許是神秘的命運使然,或許來自個人經歷與平常心。60歲的史正富,沒有像多數財務自由的人士一樣,解甲歸田享受生活,而是重新拿起書本,進行他的經濟理論研究。
“我們這代人經歷過最多的場景轉換,除了個人的努力,還要感謝碰上了好時代。”談及現在所取得的成就,史正富充滿感恩。
1954年,史正富出生在安徽的一個普通人家。12歲母親過世,父親和奶奶拉扯他和四個弟妹長大。早年生活艱苦,經歷過大躍進時代的天災人禍。
高中時,史正富由于學習成績優異在校表現活躍,被前來招兵的教官相中,破格帶入部隊。在此后五年的軍旅生涯中,成長、提干,成為最初級的軍官。
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成為恢復高考后第一屆大學生。留學期間擔任過馬里蘭大學學生會主席,對美國政商兩界有相當的觀察。之后再回國從商,股權投資做得像模像樣。2011年還曾出任過上海股權投資協會首任理事長。
兜兜轉轉二十余載,史正富心里最初做學問的想法未被澆滅,反而在時光流轉中,變得愈發明亮。
史正富說,目前公司已經過了創業期,步入平穩發展的階段,未來他本人會更多擔當教練的角色,有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去了。
“這些年在企業工作的夠久了,該學的學了,該經歷的經歷了。馮侖說,偉大是熬出來的;對我而言,幸福是熬出來的。起起落落之后,看盡了世界的復雜與丑陋,但我還是個樂天派,還是個性情中人。我想我應該把我在企業界認識到的很多事拿來和社會科學界交流。”
“我當然可以把企業做大,后面加個零,但有什么意義呢?比我做得好的企業家多了去了。我對搞學術興趣更高,幸福感更強,可能也更有社會價值。我是站在一個實踐者的角度來談學術,視角不同,問題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
在史正富內心,一件更有意義的事情始終在召喚他:做新派學術,影響一批有經歷,有余力的人回過頭來做社會科學的研究,和純學者互動,推動中國學術的升華。
“這比單純做企業,能夠給我帶來更多的喜悅。”
史正富說,現在才知道,在學校里,作為一個文人去講理想、談放下,是不難的。但到滾滾紅塵中走一趟,還能保持初心,保持出道時候的赤子之心,那才是真的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