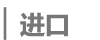|
本周三(6月25日)下午2點,成都商報“我看未來20年”大型公益演講將迎來兩位嘉賓,時尚界和藝術界的兩位大腕將聯手帶來這場演講。一位是著名藝術家,羅中立的同學、被周春芽、方力鈞、張曉剛等中國當代藝術家們稱為“葉帥”的葉永青;另一位則是中國服裝(8.31, 0.13, 1.59%)協會副會長、著名設計品牌“例外”創始人毛繼鴻。 繼王健林、單霽翔、劉永好、柳傳志、李書福、王中軍、宗慶后、王躍文、劉益謙等9位行業領袖嘉賓參加成都商報“我看未來20年”公益演講之后,葉永青、毛繼鴻是第10位、11位演講嘉賓。此次演講在金博路9號金沙遺址博物館金沙劇場,領票時間為今日15:00至18:00時,明日10:00至18:00時,有意親臨現場的讀者,請到金沙劇場售票廳免費領票(有引導標示),票數有限,先到先得,領完為止。請大家領票時帶上本人身份證,一人限領一張,并留下聯系電話,如代領需出示領取人的身份證。成都商報熱線86613333-1、成都商報新浪官方微博“@成都商報”將為讀者提供領票咨詢服務。 葉永青 讓成長變成歷史的一部分 今年56歲的葉永青人稱“葉帥”,這是張曉剛、周春芽、方力鈞等人給他加的冕。出生于云南的葉帥剃著容易在人群中辨認的光頭。盡管是四川美術學院的教授,他可以今天在北京,明天就飛到倫敦去辦展覽,然后又飛到家鄉大理去喝茶。他是畫家、策展人、社會活動家,還擔任了COART亞洲青年藝術節的藝術顧問,甚至還和劉德華一起,被評為了2005年時尚先生的候選人。 曾經:和張曉剛比畫畫 1978年,葉永青考入四川美院,那一年他20歲。從云南來到重慶,和羅中立、張曉剛成為同學。畢業后,葉永青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上世紀80年代,葉永青和張曉剛住一個宿舍,兩人每天最大的愛好就是比賽畫畫。日后,有個日本人買走了他和張曉剛各自一幅畫,每人得到200元錢。 1985年,葉永青一個人跑到北京,看畫展,同年創作《離開和留駐在草地上的兩個人》《春天喚醒冬眠者》等作品。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葉永青在北京法國大使館舉辦自己的第一次個展,他的名字也由此為國際畫壇所知。從第二年開始,他的個人畫展就如期在法國等歐洲國家登場,他本人也成為中國當代藝術輸出國門的代表人物。直到1998年,葉永青被《亞洲藝術新聞》列為20年來20位最具活力的中國前衛藝術家之一。 跨界:像鳥一樣漂泊 2000年以后,葉永青在他過去紛亂的涂鴉中選取形象,并將它單純化,鳥便成為他經常畫的題材。這些年來,他畫了100多幅鳥,樂此不疲。 這些年來,葉永青的生活也像鳥,滿世界飛來飛去,今天可能在重慶,明天就可能在倫敦,之后又可能在北京,或者又回到大理。他的工作也不局限于畫畫和教學。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在云南昆明創辦的上河藝術會館,是中國最早出現的藝術家自營空間和藝術圈。2012年,葉永青與同為云南老鄉的舞蹈家楊麗萍合作,專為其大型舞劇創作油畫《孔雀》,并在大理發起一項“鄉村藝術幫困基金”。2013年4月,葉永青以鳥元素的涂鴉為設計靈感,與時裝界大腕山本耀司合作,推出3款T恤和4款手袋。接下來,在日本和柏林都會去做專門的時裝秀。 著名策展人巫鴻認為,他在研究葉永青的創作和環境中,觀察到一種“逃離”的因素,藝術家在每一個階段從熟悉的體系中不斷離開,這樣的舉動被公眾解讀為“突破”。“一個東西從開始比較有趣,到因為環境的改變而索然無味,這是我在創作中最常遇到的困難。”葉永青形容這是“不斷拆這些墻,尋找陌生的東西,源自對邊界的懷疑”。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不斷在探索自我,藝術家的自我成長,變成歷史的一部分。 對話 “我現在就是邊走邊看” 成都商報:您一直在尋求一種突破,眼下有哪些新的想法? 葉永青:今年我想做一些手寫的東西和紙上的作品。我對新的材料比較感興趣,今年去了騰沖,看了一些做紙的手工作坊,也了解了江南等地做手工紙的地方,我希望在手工紙上做一些藝術方面嘗試。 成都商報:這也是一種跨界? 葉永青:我現在就是邊走邊看的狀態,成都演講結束后就去上海,然后回大理。其實寫作和繪畫伴隨著我觀看,好像是跨界的東西,核心是圍繞創作展開,創作的方式是書寫和繪畫。 成都商報:您現在在大理待得特別久? 葉永青:云南是我的家鄉,大理是我新的故鄉,冬天基本我都在大理。每次回去有一種回鄉的感覺,這里和北京、重慶、倫敦不一樣。大理就是鄉村,我在這里重新觀察,這種拉鋸,又重新尋找到一把尺子,互相打量,在創作、思考上提供參照。 這次回到大理,是學生等我。我是川美教師,開了一堂課叫“鄉村田野調查”, 每年都在大理上課。我自己不愿意再重復重復了30年的那種比較簡單的在課堂上課的過程,希望給我和學生開一個新的方向,這就是鄉村田野調查。在我這里我希望教學目的是不同專業,不管學建筑、設計等,從專業走出來,重新找一個視野,這就是鄉村。 成都商報:這次怎么會想到和毛繼鴻先生一起演講? 葉永青:實際是毛繼鴻先生提出的,我們經常在不同城市見面,很聊得來。毛先生的“例外”和“方所”所倡導的生活的藝術是我所欣賞傾慕的,這真的給社會開了一扇窗子。 今天的整個社會和社會生活而言,是生活和藝術的關系。首先生活在一堆碎片中,到處雜亂無序。今天來看,設計師和做藝術的有一點相通,我們都是試圖從碎片中整理有意義的東西,重新整合打撈有價值的。 至于此次演講主題,題目是毛先生在定,但我想說一些場所和精神的關系。我是最早在中國開始做藝術家空間的人,比如上河會館和創庫,我特別理解這種場所和場所所產生的精神和文化。成都商報記者 邱峻峰 毛繼鴻 以藝術鋪路 用思想制衣 2013年,“例外”紅了。“例外”創始人毛繼鴻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更是一位卓越藝術家,回顧例外品牌的創立和發展歷程,你會發現 “例外”走紅絕非例外。 毛繼鴻籍貫湖南,孩童時代在服裝廠長大,求學于北京服裝學院,成為一名服裝設計專業畢業生。第一份廣告人工作,讓他接受了最初的商業啟蒙,但他總是堅持用藝術去做商業,并用商業推動藝術。 曾經:服裝廠長大的孩子 現在來看毛繼鴻的人生軌跡,他進入服裝業似乎不是例外。 1969,毛繼鴻出生于湖南,因為母親是一位服裝廠廠長,他從小就在布料、縫紉機和裁縫的世界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便與服裝設計結緣。 上世紀80年代末,毛繼鴻考入北京服裝學院,在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波文藝熱潮中,毛繼鴻在這里接觸到了以徐冰、劉小東、喻紅等為代表的當代藝術家。1990年,毛繼鴻南下廣州,在一家廣告公司謀職,并作為副導演拍攝了TCL[微博]的第一部電視廣告片。多年后回憶起這段最初的商業啟蒙階段,毛繼鴻的記憶仍很清晰。 “這個過程對自己刺激很大,那時候就在想特許經營。”離開廣告公司后,毛繼鴻前往香港幾家公司上班,并進入當時熱門的外貿服裝行業。一年之后,由他和人生知己馬可聯合創立的“例外”服裝品牌順勢而生,這是1996年。 “例外”:走紅并非例外 1996年創立“例外”時,毛繼鴻通過市場調研發現,當時中國的原創設計品牌太少,定位低,他于是瞄準了高端女性服裝市場。“我們的顧客,和我們一樣,都是從過去完全斷緣的文化上面建構起來的知識結構。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夢,不管是錢鐘書的夢還是李玉堂的夢,還是沈從文的夢,都有這樣一個過去的夢想。”在毛繼鴻看來,“例外”給了這些客戶一個特別好的詮釋,去抒發自己對文化藝術的情感。 創辦17年來,“例外”一直在小眾圈內“默默無聞”,直到2013年一夜爆紅。紛至沓來的媒體,開始在廣州的大街小巷尋找“例外”辦公地,幾天時間數百個采訪請求如潮水般涌來,一度讓毛繼鴻嚇得“躲”了起來。 “例外”幾乎從不做廣告,也沒有形象代言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例外”不做營銷,而是選擇了另一種文化營銷。 2011年,毛繼鴻創立的“方所”開在了太古匯這個廣州最高端的商場,這個占地1800平米的空間是書店、美學生活用品、服裝、展覽空間與咖啡的復合體。在毛繼鴻看來,知識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希望通過這個載體帶給更多的人機會。 事實上,“方所”已經被譽為廣州文化新地標。 2012年,毛繼鴻聯手香港藝術家創立又一個全新品牌“YMOYNOT”。毛繼鴻說,他希望通過YMOYNOT這個品牌,建立以東方美學為核心的亞洲設計師平臺,推動年輕一代創意設計力量。 對話 “做把情感轉化為才能的人” 問:“例外”是一個很特立獨行的品牌,未來是否會針對大眾去設計? 答:“例外”在一直不斷的堅持自己的探索和實踐,現在讓我特別欣慰的是———現在十多二十歲的小孩,成為了我們的粉絲,一些爸爸媽媽會過來找我說:“哦,我的女兒是你的粉絲。”這點讓我覺得很開心,已經得到了年輕人的反饋。 問:現在有很多追求規模、追求快速資金回籠的“快時尚”服裝品牌,受到很多年輕人的喜愛,對于這些品牌的經營模式怎么看? 答: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經營模式,我只想我自己的經營模式是讓我覺得很舒服的。 問:如何看待當前的創業環境? 答:我不希望所有生意人都唯利是圖。不喜歡企業家動輒問,你有多大的企業,永遠只講大,講規模,講什么時候上市,而不講質量和創新。當今社會其實在用一個單一的標準去衡量企業家成功與否,例如企業的“知名度和規模”。 問:你在發展過程中感覺到的最大危機是什么? 答:我感覺最大危機還是在價值觀上的危機。不管是企業家、還是員工,都存在著互相不信任的大環境。我們的價值導向太以錢為標準來衡量一份工作,缺乏價值觀和信仰上的統一。 問:你對個人的未來生活有怎樣的規劃? 答:作為設計師和企業家的雙重身份,未來會更偏重于把自己定位為“把情感轉化為才能的人”,會組織更多愿意做文化創意事業的人,在這個平臺中發揮價值。我覺得我更多是一個背后的人,而不是臺前的人。 |
????